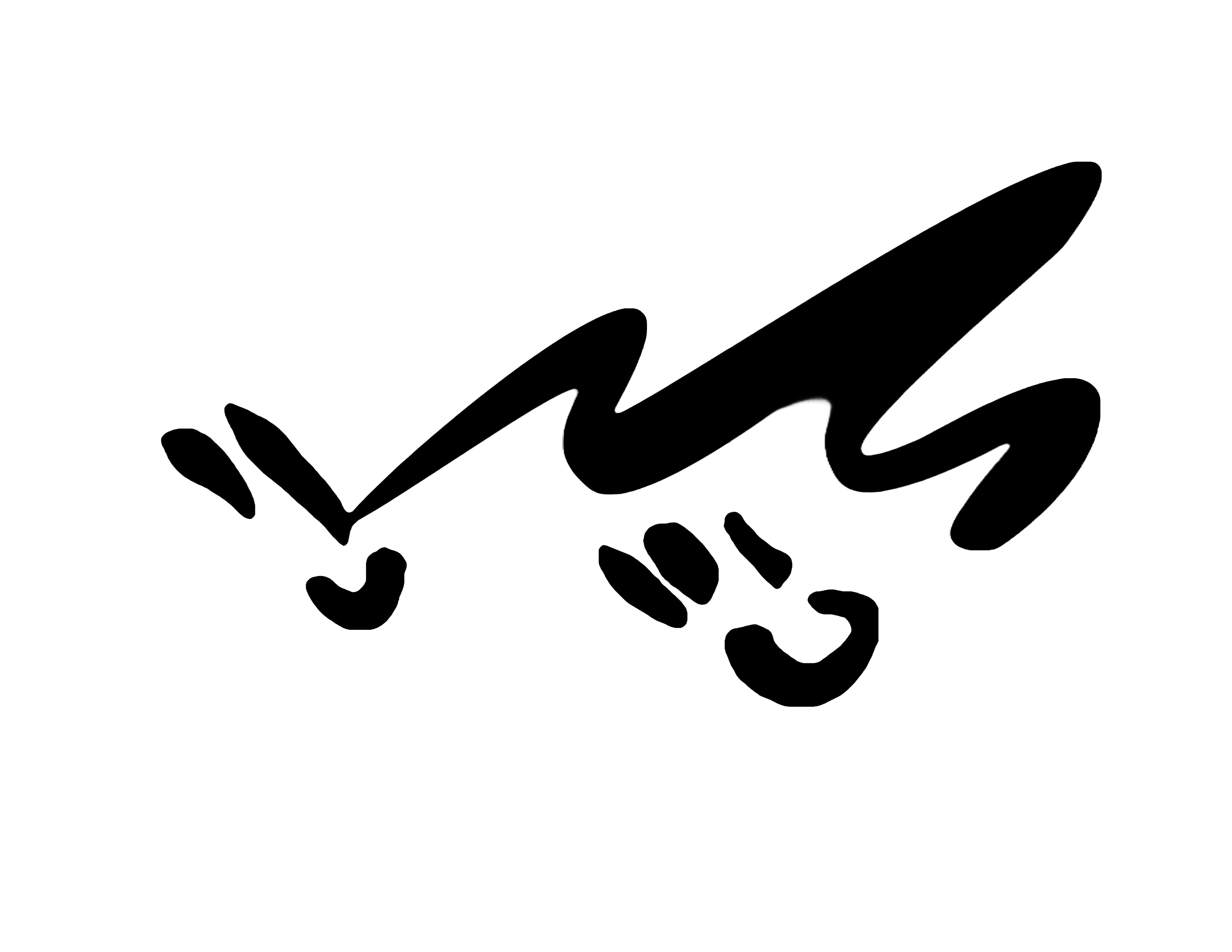饿
Oyster Pail

编者按
去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应该是一个人最本能的冲动了。得吃下饭去才能活着呀!活着这件事又反过来给“饥饿”这件事披上层层隐喻——我们吃下饭菜,吞食下一段经历,经历又变成记忆。于是记忆和食物深深挂钩了。食物不仅物理意义上组成我们的躯体,更是构成了历史本身,是“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凭据。
“吃”可以是一种抵抗吗?在无法改变外部世界时,我们顺从,并坚持喂养自己,让热腾腾的吃的滑下食管、跌进胃里;我们伺机而动。然后逃进陌生的环境之后,又发现自己的习惯开始被重塑。可并没法真的回归故里,于是对家乡食物的渴望连带着的是更加看不见、摸不着,难以言说的愁绪;用语言勉强能够描绘的烦恼正是身体在一五一十地承受——“想念”化作真真切切胃里的绞痛。
“Woe to you who are full now, for you will be hungry.” (Luke 6:25)
坐在去纽约的火车上胡思乱想时,常常忘记自己已经不在北京上高中了。那时候每天来不及吃早饭就赶地铁,几百号通勤的人一起在一号线灰白的车厢里,我陷入饥肠辘辘的睡眠。从家到市中心,再醒来已经跨越三十公里。北京十二月的寒风中,从西单地铁站到最近的便利蜂,是我这辈子走过最漫长的距离。拖着冻麻了的四肢挪过去,用最后一丝力气和店员说:“魔芋丝,萝卜,鱼豆腐,甜不辣,杯装的。麻烦您先给我吃一口再结账——我快低血糖了。”
吞下一整杯热气盈盈的关东煮,感官才随之复活:萝卜鲜甜,豆腐柔软。吸溜着魔芋丝喝着西北风一路从便利店吃到教室。年级主任不让我往垃圾桶里倒剩饭,我挑衅似地一口喝掉滚烫的汤汁,朝他亮一下杯底才丢掉。数学老师开始讲无穷级数,我吃饱了,陷入无穷梦境。
高中时的我每天都在用实际行动演绎“倒头就睡”四个字,上下课铃声对我毫无意义。数学课被微积分催眠,英语课被Allan Poe吵醒。总是毫无理由地感到精疲力竭,去卫生间照镜子,额头老挂着个红色的桌子印儿。有时候忘记要换教室,睡醒了从桌上抬起头,屋里静得出奇。大家都去上课了。有人贴心地给我关了灯,微风吹起蓝色窗帘,混着柳絮和尘土的气味。我披着校服外套呆坐在黑暗的空教室里,感觉像是放弃了某种对抗后,顺着坚不可摧的铁壁滑下来,缓缓落上一块名为遗忘的果冻。
此时往往已经把午休时间睡过去了。我在门口保安处蒙混过关,翘课去和府捞面吃“下午饭”:番茄香草汤猪软骨拉面,多加香菜。嘎吱嘎吱嚼碎猪软骨,舀起一勺鲜红浓郁的番茄汤底——是预制粉兑开水,痛饮一大碗的时候有饮鸩止渴的悲壮。当然,吃多了碳水化合物带来的瞌睡不可避免,所以趴在面馆桌子上又睡晕过去了。醒来沿着地铁一号线游荡,思考下一顿饭。
迷迷糊糊三年过去,和府捞面关门大吉,我也终于被迫投入新生活。
火车到penn station换乘地铁。站在时代广场-42街著名的路口,风从路面的铁格子吹上来,掀起我的衬衫,地铁站的氟味混着大麻烟味,无序感先侵蚀肺部。我开始对纽约人文地理上瘾,无休止地看“Becoming a New Yorker”的博客,研究曼哈顿格子,研究Broadway tickets and how to get ‘em cheap。到感恩节假期时,我已经学会像一个纽约人一样目不斜视地在街头快走。观光巴士的司机不会再拦下我,问我要不要参观自由女神像。
自然也学会了带朋友们趁放假到处找好吃的。一个月没吃亚洲菜的我们从昂贵的寿司店里走出来时神清气爽。空洞感被大量新鲜生鱼片填充,我不再饥饿,好像也因此不再被突如其来的悲伤,困倦或虚弱侵袭。纽约的冬天和北京一样冷,但我头一次感觉和世界产生了健康的隔阂。原来饱足感能让细小的情绪变得遥远:生活,学习…一切如此完美,除了难以吃到熟悉的饭菜。没关系:越是珍贵,吃到的时候就越幸福。我感觉自己像九十年代的情景喜剧女主角一样振奋起来,也像她一样,在曼哈顿的冬风里矫情地裹紧了新买的大衣,咬一口wholefoods的有机苹果,感觉自己找到了万能life-hack——吃好。
食堂很难吃,但“人是铁饭是钢”,我尽量抓紧一切能充饥的食物:加过量奶油芝士的意面,水煮鸡胸肉拌黄瓜,菠萝披萨用大杯Mountain Dew冲下食道。如果早饭有油炸土豆小丸子,我宁可第一节课迟到也要吃完一盘再出门。没有什么比吃饭更让人心情愉快了。我不再无缘无故感觉疲倦,开始有力气努力生活:练习用英文讲笑话,即使偶尔screw up the punchline;压力大时候就去镇上唯一一家川菜馆子,花北京三倍的价钱吃根本就不辣的毛血旺;带美国朋友坐火车千里迢迢去隔壁镇上涮火锅,教他们用筷子吃毛肚(七上八下,蘸芝麻酱),教人说中文,你-好、谢-谢、我-饿-了。带牙套后长达两周什么都嚼不动,只能薄荷巧克力冰淇淋做主食,吃一个scoop就可以半天不饿,学习时精神抖擞。实在太痛苦就点一份蟹黄豆腐外卖,印着红色琉璃塔的白色小纸盒*看起来如此亲切,我一边担心牙痛得掉下来一边感动得狼吞虎咽。蟹黄酱和米饭粒很不体面地卡在牙箍里,我一手扒饭,一手写邮件,和助教就数学作业扣分问题大战五百回合。

(*Oyster pail是这个,相信留子们都不陌生)
期末考试后终于可以午睡,和朋友约好睡醒去吃川菜。这里总是下小雨,我的梦里也湿润:我梦见自己独自坐在高中的空教室里,门窗紧闭,脚下有积水慢慢上涨,我的双脚关节开始生锈,双腿爬满青苔。太冷了,所以我拆开一大盒炸薯条往嘴里放。每次中午来不及吃饭就会吃这个:熟悉的油腻咸香,土豆淀粉如一条河温暖地流经身体,出国前很少吃快餐的我,一来这里就爱上了美国comfort food。
冷水淹没膝盖,我想做一碗卤肉饭吃。第一次自己炒糖色没掌握好时机,焦糖糊在锅底上滋滋冒烟,引得厨房报警。好在炒出来不错:卤肉丰腴,青菜消瘦,连锅上的糖油混合物都被我刮下来抹面包。不小心把切洋葱的手抹在眼睛上,一下子手忙脚乱泪如泉涌,于是水也一下子涨到胸口,我勉强浮着,惋惜地看着H-Mart买的小电锅在水里漂走。
胃里胀痛但仍然饥饿。吃点什么呢?手心出现一颗糖炒栗子:滚烫的,甜的,北京冬天唯一的好处。小时候我妈会买一包新炒的栗子,放在羽绒服左兜里防止变凉,把我一只手揣在右兜里,剥好一颗一颗递给我。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每天能吃上糖炒栗子,第二大的梦想是去大洋彼岸念最好的大学,殊不知这两者无法兼得。我迫不及待地拆开放进嘴里,想象中的甜味没有出现。我被烫的满嘴燎泡,食道生锈一般无法吞咽。没顶的水阻断空气,眼眶里长出水草。我用力咳嗽,想把栗子吐出来,却呕出来一串内脏。
…
我一骨碌坐起来,咳得惊天动地。室友惊恐地看着我:“Are you OK? Are you still going to dinner?”
我确认了一下自己的五脏六腑的确还长在一块,说:“我没事,就是睡迷糊了。”又一顿咳。
室友依然一脸迷惑:“I don’t understand. Are you OK?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我一字一顿地说:“我真没事儿,你们去吃中餐吧,我再睡会儿。”
她迟疑了很久,还是说: “Honey, I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 are saying.”
…
哦。
才意识到,她确实听不懂。和外国人说一堆中文真是“睡迷糊了”的最高境界。过去一年仿佛一场自我欺骗的大梦,在梦里假装什么此心安处是我家。每次和父母打电话都只敢抱怨饭菜,同样的话反反复复说一个小时,好像一切困难都汇聚成“饭难吃”三个字。他们也只能心照不宣地说:“不要在吃上省钱,有空就出去找中国菜。” 好像吃下一份熟悉的食物,一切异国他乡的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
衣食无忧的小留学生,离世俗意义上的艰苦多么遥远。但是,没有一天不在撕心裂肺的饥饿中度过,因为深知离家了就再也回不去。小小的不安,小小的辛苦,小小的思念和孤寂,无数情急之下脱口而出,抑或是想不起来的中国字儿,变成无数个惊醒的清晨夜晚,和一场下着雨的无穷梦境。这些该如何细数,如果多说一句就像是不知感激的无病呻吟。好在,好在还有美食。口腹的餍足像一剂局部麻药。但是无论,无论我怎样说一万句你好/谢谢/我不饿,怎样魂牵梦萦,一顿毛血旺、涮火锅、卤肉饭,还是日本寿司越南米粉,我怎样花钱,怎样乘车逃跑,怎样暴饮暴食,这次,这次都不能让我醒来。
所以我说: I’m perfectly fine. Don’t wait up. 然后在室友释然的表情里裹上被子抵抗胃绞痛。
一年份的疲惫找上门来,我又睡去。在梦里游荡到湖边,树林里传来列车鸣笛的声音,我把后脑勺靠在铁轨上躺好,双手合十闭上眼睛,陷入虔诚饥饿的等待。好像十六岁一个平常的晚上,我学累了,等待我爸做的挂面宵夜:热锅冷油,下葱姜蒜爆香,鸡蛋滑熟,大碗开水倒下去加面。一切劈里啪啦归于寂静,只剩雪白混浊的面汤,热气氤氲,凝在冷窗户上,流下一滴泪。
2024年8月26日于北京

NEXT: 传统文化与现代危机
东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