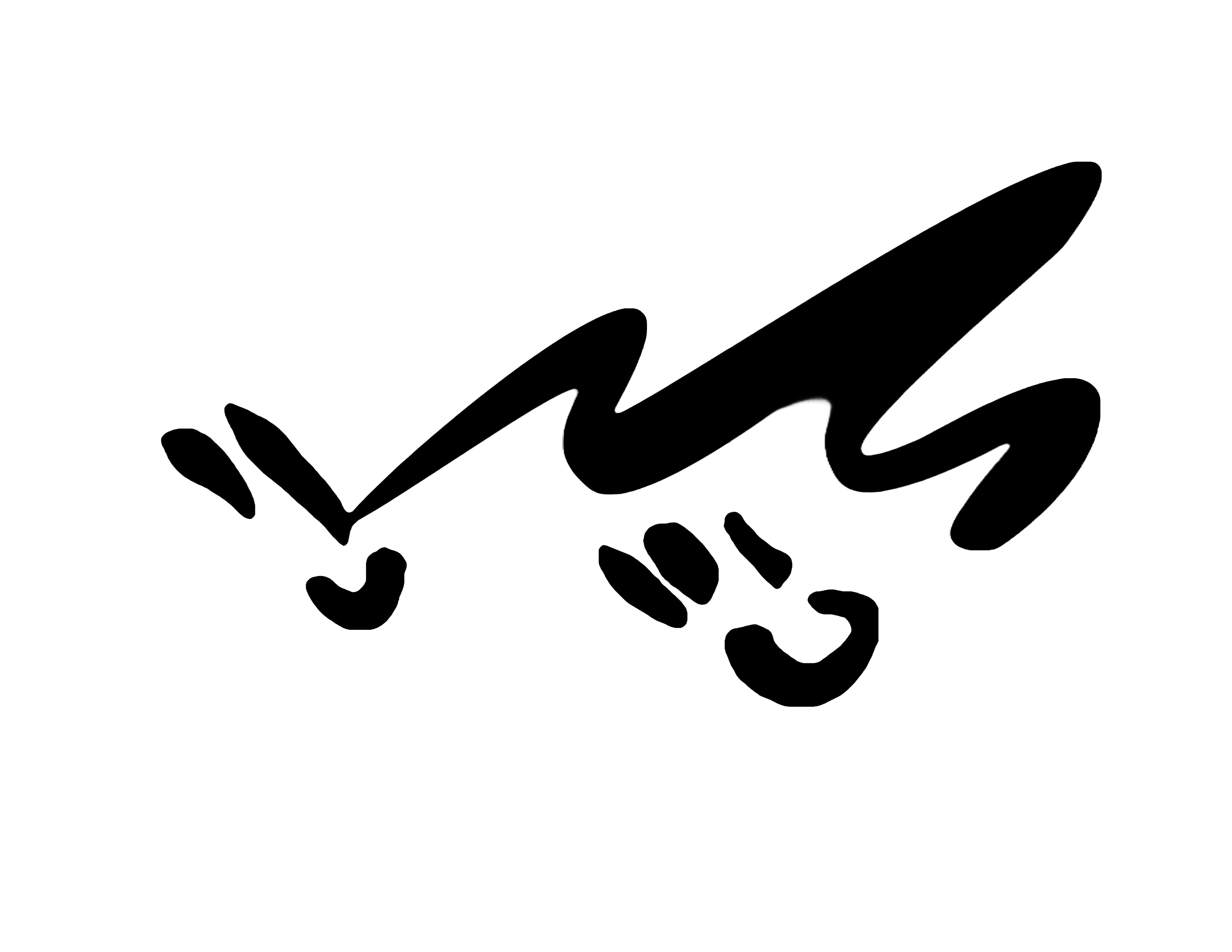三棱镜
罗润浩

编者按:
本文以“镜像”为核心主题,是一次将现象学及精神分析理论融入文学的尝试。作者以三个角色刻画出同一个人的三种不同面向,暗中对应了拉康三界。随着想象、实在、符号三者间的界限愈发模糊,珠江的夜晚也便成为了主角精神世界的外在映射。
夜的寒冷很短暂。叶影勾勒出的江畔小道稍微清晰起来。江水也别样清澈:似水草的黑色丝絮铺满江面。这团黑色上还浮起沿岸暖黄色灯光和一个不断波动、勉强维持圆形的月——我已经不再见到他了,倒是这其中分明还有我的脸,也或许是我的镜像。
所有反光物上都能看到我的镜像——我其实不太同意:这镜像的头发分明比我长许多。
与他初识的时刻还未完全入夜。珠江边上被红黄相间的夕阳引出通达幽冷的晚间庆典序幕:那外放的喇叭随着人群跑步的声响越发喧嚣;正直播的电台节目和沉寂在储存卡里的DJ版民歌彼时并进。 我们始终在走,沿着海印桥走到江对岸,又从海珠桥走回来,显然两边的人流也是如此相互晃动,但依然寻不着安静的地方。
我们相识的地方正是这条沿江路。那夜与此夜出奇的一致,一路上只有稀疏的人影和一些细碎的鸟叫声,时不时有些江风打在榕树的根须上。同样是微弱的暖黄色路灯,但那夜颇热,热浪甚至把光放大了不少。
海珠桥桥底的过道不长 ,约一百米,又刚好把暖光全聚拢于此。和此夜一样,那夜也是有着一 个木制手推车。在手推车后面,依靠着桥墩站立的是一名穿着粉色绸质衬衫的男子,满脸络腮胡 的头上留有长发。顶上挂着一个灯牌,歪歪扭扭地闪烁着“那夜凌晨”四字。
依稀记得这是他领我来的地方,说“那夜”、“凌晨”两个词的不确定性扑面而来,到底是哪一夜,又到底多少点算是凌晨,流动摊贩今天和明天的位置都不一定。
酒摊的吧台立着一张A4纸打印过塑的告示牌:
1、本人完全不喝酒,更不会陪酒;
2、假若你的叙述足够彻底,请你一杯也未尝不可;
这是此处唯一明确的东西。
我确信他的故事很动听,足以写成传记那种。我们吹着水,从沿江路一路走到沙面——无法相信面前这个总爱讲诸如“遇到陌生的路要往右走,因为右永远是Right”这类冷笑话的长发男子, 在入夜的几个小时前,才刚挣脱出来。
“从家里挣脱出来”,他如是说,声音如风打在榕树上一样自然顺畅:自母亲离婚改嫁后,父亲 便有双相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等症状。
“不知是离婚前还是离婚后,那时候还没有记忆。”——可能是酒后被江风侵袭的缘故,我们的脚步犹如舞步匍匐前行,还颇具美感,一时间甚至觉得沙面钟楼上的明月也在拉着我们喝酒—— 严重的症状应该是离婚后,他忽而又想起来,陪饮的月瞬时被他赶走——有记忆时起听见的仅仅 只是父亲天天在痛哭的声响,以及晚饭时人们絮絮叨叨地说着“一个堂堂男子汉,哭有什么用”。大约小学四年级以后,得知原来这是一种病,和感冒发烧一样所有人都有可能得的病,而非“傻的”、“痴线”。之后,他方才极力在家里的大疯大癫与正常秩序之间寻得些许安宁,直到几个小时前。
那个粉色衬衫、满脸络腮胡的是酒摊老板,但他不愿意得此称谓:他自称没有人愿意彻底聆听, 除了他以外,所以他是一个职业听故事的人。
他说所有值得沉醉的夜晚都需要燃料,要么当一个彻底诉说者,要么当一个彻底聆听者,否则只 是一种煽风点火般的附和。
我问这个人什么叫彻底聆听,他说聆听的最终目的是复现世界的事实,当足够彻底地聆听之后就能彻底复现他人。不彻底的聆听是一种附和,是一种不自量力企图介入事实的狂妄自大。
这所谓彻底聆听的人,却不愿意请他一杯酒。我问这个人,难道他的故事不动听吗。他开始洗杯子,或许是开始彻底聆听了吧。
那夜的几个小时前,他的父亲又一次发疯,无数过往经验告诉过他,无论如何极力阻止,也无法 阻止这个疯癫的人砸东西和狂笑。即便控制住疯癫的身体,也难挡父亲疯狂地辱骂他的祖父和祖 母。
我们已经走到了沙面的一角,路灯近乎被树影完全遮盖,沿着阶梯往下,紧挨着江水有一片刚好 够两个人躺着的露台。我们躺在上面,眼前只有硕大的月亮。
“屌你老母,废柴”,他突然在模拟他父亲的口吻——他的手拍打旁边的江水,目光似乎在看着水流从手指缝中滑落—— “我老母就係你阿嫲。”——又一次打在江面上——“我就係屌你老母,吹啊,废柴。”
这夜实在朦胧,月光下仅能见着一个黑影不断在嘶吼与颤抖之间切换,每次击打水花都是他冷静 下来进入下个角色的节拍。
偶尔一阵风吹过打断了我听他叙说的思绪。原来月亮已不在我们头顶,才意识到原来他已经在断断续续地扮演了他的往事许久。稍微分神后,我又继续沉入他的叙说中。
所谓彻底聆听者没有回答我,只是看了我一眼便继续擦杯子,用调羹在空的调酒壶里打转。 我越发盯着他的眼睛,调羹打转的速度越发快了起来。他不断在闪躲着我的目光,然而却因此更像黑洞一般攫住了我——我从这个所谓的听故事的人眼里看到了我的镜像——不断闭语,不发出任何声音,这个长发的人坐在酒摊前静默地等着酒。
调酒师倚靠着墙面。月光从桥洞投入,却躲不过满桥底暖黄色的路灯。尽管有充足的光,也仅见他的嘴巴微微抖动,五官没有任何反应。他似乎说了些什么。
调羹仍没有停下来,依然在空转。
他突然喘着大气,呼吸声比风还重,又霎时安静了下来。这股宁静甚至显得月夜都喧嚣了,缠绕 着月的云也显得尤为吵闹。
“就这样,我爷爷走了,”我也深深吸了一口气,忽觉所谓彻底聆听似乎指的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说些什么,索性就不说话了。
正准备长吁短叹,把那个深吸的气化作一声“唉”,他忽地笑了一下:
“嘿,也挺好,能去那边保护自己的老母。”
我也跟着他笑了一下,就像他说右就是Right时一般。
还记得那夜在此时即将结束,月亮仍在,但抵不过即将出现的太阳。随晨曦渐近,它悄悄隐没在亮光中。日光渐渐使他的脸显现出来:他面容的轮廓一如刚见时他自称终于从家里挣脱那般惬意,那般清晰。未待我问他何以挣脱,他说:
“我想彻底冷静一下。”
我还记得他的这卷长发,就如同我的镜像一般站在我左手边的露台上。
他的故事确实值一杯酒——酒摊里的那个人依然在空转着瓶子,他给我解释这一步是stir:适用 于烈酒特调,轻柔地混合一切,而不破坏酒体。
所有的反光之物都在显露我的镜像,无一例外,包括在那空的金属调酒壶上,那个所谓彻底聆听 者的手腕仍在上面打转。
这位调酒师说我的故事也值得换一杯,开始往杯里加入冰块。然而我只想为他讨一个公道:“那 他的酒呢。”
倒入了些调配酒和基酒,他开始stir了起来。那夜与此夜出奇一致,只要他想当彻底聆听者时就彻底不语。
离开布满暖黄色灯光的桥底后再看向江面,更觉江水轻柔。我带着他给的酒,双肘倚靠在江边的栏杆上。深褐色的酒液在通透的大方冰中变成冰块的陪衬,如同月光之于江面。 他也跟了过来——没有任何声响,说要陪我喝一杯。之后用左手接过我的酒,目光跟随我的目光,一同盯着我们的镜像。
昏暗下,微风不禁向我们吹来,它为打破酒摊的所有规矩而庆祝,如此夜里直教人打冷颤。除月 亮外,所有东西都显得朦胧了起来——包括镜像,在酒精过后尤为如此。
江水朝低处飘荡,后浪不断把前浪往下压,所有倒影浮游在上,渐渐也被冲散了形体。此后再也 没见过他了,只发现我的镜像。
它的那卷长发愈发清晰,江水似乎顺着脚踝,慢慢抚摸上膝盖。纵然是南方,此夜里的水也是格 外寒冷,寒冷得直叫人冷静起来——比过往任何看向这幽暗而又深邃的黑色江面时都更为冷静, 冷静得发现这些镜像渐渐开始是他的脸。
他的脸慢慢被后浪压下,我们如水墨般散开,仅见他不断沉没江中,彻底投入了他的冷静。

NEXT: 异乡人
飞越边界_YUu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