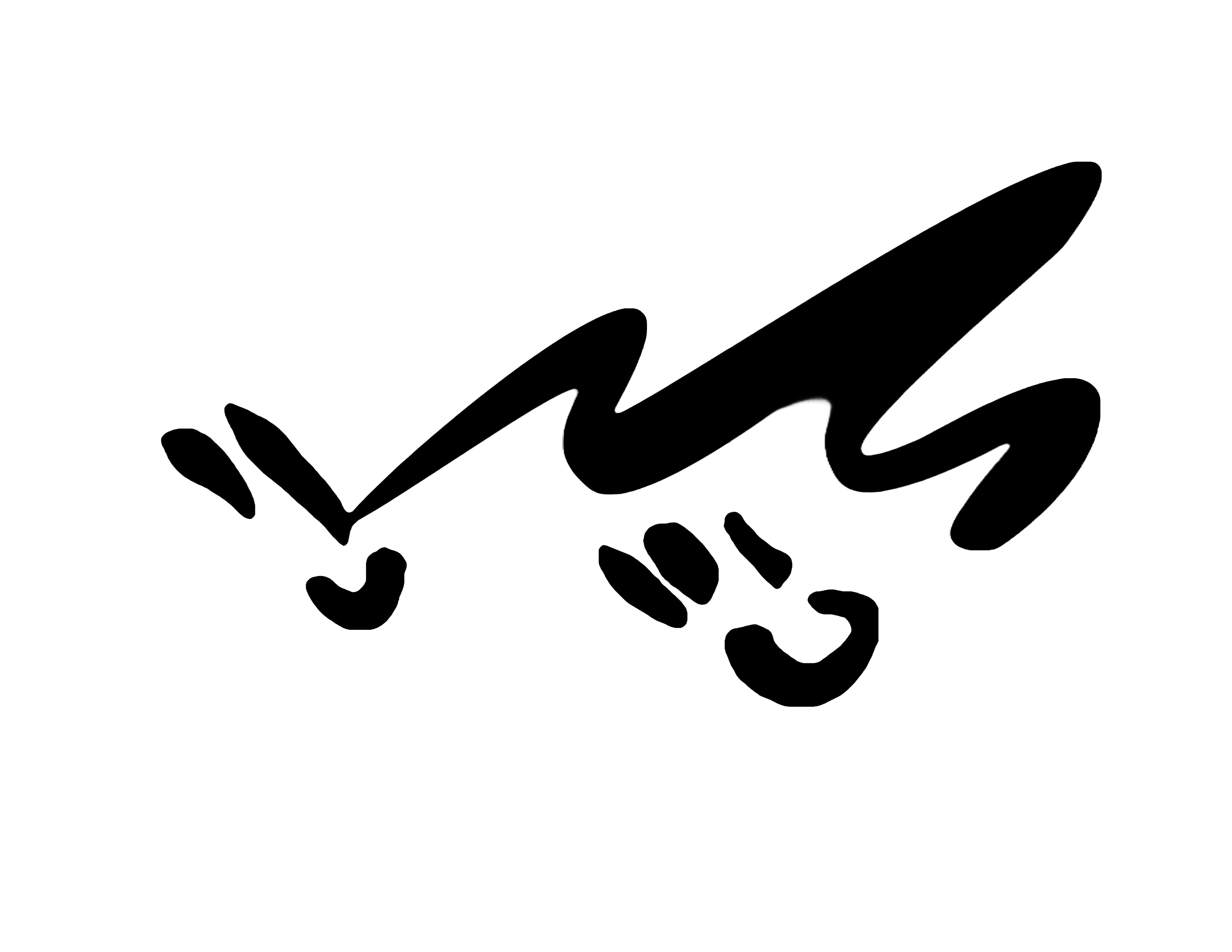当一个00后开始怀念90年代
麦芬

编者按:
被历史幻想构建出的情绪,又何尝不是一种作为虚构本身的真实呢?当零零后的确开始怀念九十年代,他们所怀念的从一开始就不是某种真实的经历。你可能会说,这只是想象罢了,甚至批判其为逃避的手段。而或许正因为在切实的经历中看不到更值得期待的光线,如此这般那个作者所推敲过的,实则远不如现世的欣欣向荣,才变得色彩鲜艳起来。语言作为我们共有的秩序,其所带给作者的也绝不仅仅流向一人。当这种怀旧情绪得以被你我共情,哪怕是字面意义上被理解、认同时,我们就已经承认了这一束情怀的真实。现在,年轻的我们开始把希望都投射给古老——这或许是一种微妙的信号吧。
去年《繁花》大热的时候我也在看。全剧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片段既不是黄河路的灯红酒绿,也不是弄堂里的人间烟火,而是第九集,宝总拿下第一张外贸订单后与小宁波击掌相庆,兴奋地大喊,阳台上的汪小姐也发自内心地为他们高兴,讲他们是“戆(傻)人有戆(傻)福”。导演随即一个低位镜头,切到了宝总在洒满金黄的街道上追着小卡车跑,看不到人脸,只见摇晃的风衣下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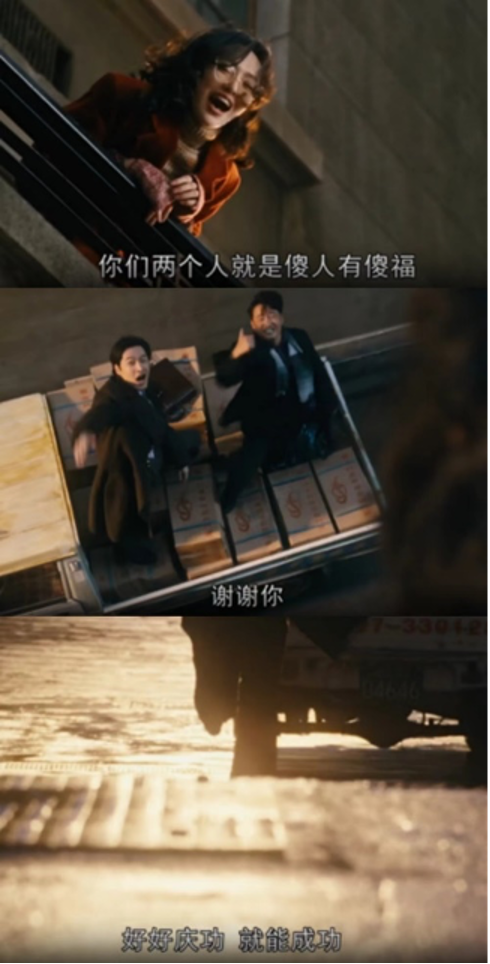
就是这一幕中的某些东西瞬间击中了我。不是王家卫的打光,也不是宝汪的甜度,而是某种乡愁混合着怀旧的心绪,带着点儿温暖,带着点儿轻巧,一些从未拥有但已然失去的东西。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那是什么。那是90-00年代人们特有的朝气、希望、生命力,以及——这话从我一个二十来岁的人嘴里说出来可能略显滑稽——年轻。
我想,作为一个00后,我好像确实有点怀念90年代。
可是,人怎么可能怀念起一个自己从未亲身经历过的时代呢?我对于那个时代的印象,难道不都是经由各类影像、文字与口述层层叠叠建构起来的吗?我是否只是在不知不觉间被某种怀旧情绪(nostalgia)所捕获,结合了对现实的不满与《阳光灿烂的日子》式的想象,创作出了一个从未于真实历史上存在过的“90年代”?糟糕,我好像也变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种整天吹嘘过去有多好的人,甚至比ta们更早了开始了二三十年。这可能就是我们东亚人,连倚老卖老都要从娃娃抓起。
到底是哪个“90年代”值得怀念?
当我们说“怀念90年代”的时候,90年代究竟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怀念?如果我没法给出一个答案,那这种怀旧情绪便不具备任何合理性,从而变成必须舍弃的对象。
首先排除最明显的错误答案,即物质水平。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1995年的GDP是7345亿美元,而这个数字在2022年是179600亿美元。即便扣除约208%的累计通货膨胀,这二者之间也没有任何可比性。
抛开抽象数字来看具体生活,我们今天所享有的物质水平也是90年代的绝大部分人们完全没法想象的。在90年代,一顿麦当劳的价格差不多是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一个月的工资,而今天你只需要花13块9就可以点到一份穷鬼套餐。在当时,世界范围内最新的流行音乐几乎不在市面上流通,往往一张打口碟,即已进行损坏处理(用专用机器把光碟切掉一段)却又因为各种各样原因流通到中国的碟片,便能让年轻人们如获至宝;而在2024年,你只需要一部充话费送的手机与每月18块的网易云会员。虽然今天中国的贫困依然触目惊心,可是至少绝大部分人能维持基本的温饱。这很大程度上是最低生活保障,即低保体系的功劳。然而,低保在1999年才基本覆盖全国范围内的城镇在岗职工,农村低保则要等到2006年。
很多人或许会说,以上对经济发展的称颂仅仅是从城市中产阶级及以上的视角出发的,而与此同时,广大农村居民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如快递员、外卖员、农民工等,依然面临着较低的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以及极为有限的社会保障,在资本与权力的剥削前几无抗拒之力。例如,外卖骑手经常要面对严寒酷暑,应得的极端天气补贴也时常被克扣,甚至被算法逼迫着冒着生命危险超速送外卖,即“被困在系统里”;在2024年的今天,用人单位拖欠甚至克扣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能成功维权的反而是少数。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然而,我们同样不得不承认,就算是被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其工作环境和薪资水准与90年代乃至00年代的外来务工人员比起来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善与提升。在当年那起引发了全国轰动的山西黑砖窑案中,警方解救了300余名民工,他们有的是当地砖窑矿主从人贩子手中购买来的民工,有的是被拐卖的儿童,其中不乏残障人士。这些民工被关押在砖窑矿场中,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条件下从事极端繁重、危险的劳动,动辄被暴力殴打致残致死,是字面意义上的奴隶。这起案件发生在2007年,而黑煤窑、黑砖窑在90年代乃至00年代都属于相当普遍的现象。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当今外来务工人员应当为ta们的工作条件比起过去来有所进步而感恩,更不意味着由我们所组成的社会对ta们所负有的责任有任何程度上的减轻——如果今天比起过去来显得有很大进步,那仅仅说明过去的标准太低了。
那么,90年代在上层建筑层面,即法治、开放程度、社会正义、文化产出等方面又如何呢?虽然没有经济层面那么确定,但我认为,至少在大多数可量化、可比较的标准下,今天的上层建筑相较于90年代也进步了许多。
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因为外出上网时未携带身份证件,被广州市政府执法机关当作三无人员遣送至收容所,最终因反抗而被收容所工作人员殴打致死。这一事件直接推动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彰显了法治的巨大进步。至少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一个大学生会因为出门上网未带证件而被送进收容所,乃至殴打致死。2022年,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引起了巨大轰动,再次提醒了我们,中国女性群体依旧生活在一个危险无处不在的父权社会中。然而,这起事件打碎了许多女性对于安全的感知,或者说错觉,却也反过来说明了许多人至少生活在会引起这种错觉的环境中。换言之,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在2022年至少会引起公众的震惊,但如果换在90年代则根本不会,因为在当时每天都有无数起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在发生,整个社会对此处于一种几近麻木的状态。飞车党、砍手党、车匪路霸…这些落在纸上只是轻飘飘的几个词,但放在90年代,每个词背后都是无数百姓的血泪史。后疫情时代,外国人来华数量虽仍未回到疫情前的水平,但比起90年代仍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人出国数量则更不必说——按需申领护照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事,而在此之前,个人护照的发放需要相关部门进行审批。
如果以基尼系数进行衡量,90年代在收入平等方面的确远胜于今天。不过在社会整体收入水平远低于某个标准线的情况下,谈论收入平等的内在价值似乎并无太大意义。文化产出方面则更难以衡量比较:一方面,新旧潮流交替冲击之下,中国社会的头部文艺创作曾在质量、先锋性、开放程度等方面到达了一个我们至今都无法逾越的高峰,相比之下我们今日的文艺作品反而显得空洞无力。崔健的摇滚、北岛的诗、《霸王别姬》、《我爱我家》、《阳光灿烂的日子》……但另一方面,今天文化产出的多样性和普及度却又远超九十年代。我们时常吐槽古装剧和短视频的千篇一律、陈词滥调,但“能让普罗大众享受的文化产品”也不过是近二十年的新发明,而角色扮演游戏策略游戏卡牌游戏任君挑选,在90年代也是不可想象的事。当然,“我们是否需要这么多选择”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时代的反曲点
文章写到这里,不只是读者,连我自己都要发问了:明明开头自称要写一个怀念90年代的00后,为什么全文大部分笔墨都在讲90年代有多糟糕,活像是在回顾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尽管其过程看似和主题背道而驰,但我依然坚信,当且仅当一种直觉经受住了最猛烈的质疑、解构、拷问时,它才具备继续坚持的价值;唯有当你破除了那种人们习惯性施加在想象与记忆上的粉饰,却发现自己依然保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才能真正得见你此前未曾发觉的坚持它的原因。
作为一个社科脑子,我会下意识地用定量或定性的数据与标准去说明一个社会问题。但不得不承认,在一些对于我们而言很重要的问题上,数据与标准或许的确力有未逮,例如下面我对于本文核心问题的答案:尽管今天在几乎一切可量化可比较的指标下都要优于90年代,但90年代的年轻人们相信明天会好过今天,并且“后天好过明天的幅度”会高于“明天好过今天的幅度”。用数学语言来讲,就是90年代生活的二次导数为正。即便贫穷,即便封闭,但人人都能感受到新时代的大幕在缓缓拉开——只要有希望,心里就还有口气在,四五十岁的人也就还年轻。
而00后怀念90年代,正是因为我们感受到时代的反曲点已经来临。许多人会把这种怀念归结于当今的高房价、阶层固化与不断加剧的内卷,但要我说其实不仅如此:GDP和收入还在涨,我们和国际社会的交流还在缓慢回升,一些细节还能让人感觉到社会微小却坚实的进步——但倘若在不远的将来涨势停滞,潮水退去,恐怕也不会有多少年轻人会为此感到惊讶。这种感受是由一些特定的迹象引发的,但却多少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站在更高角度,把当今时代作为历史上的一点来看待,其实也很难用理性证据证明我们已经越过了那个反曲点,但不知为何,somehow,大家心里就是知道某个时代已经永久地过去了。所以今天的年轻人躺平、佛系、焦虑、抑郁、乖巧、沉默,却唯独不像年轻人那样,对一切感到生机勃勃。当然,我或许也没有资格去定义年轻人,甚至不好把任何形容词套到这么大的一个群体上。
2022年,李克强总理在即将卸任之前,在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说了这么一句话:“改革开放不会停顿,长江黄河不会倒流。”我们衷心地希望,长江黄河不会倒流。

NEXT: 饿
oyster p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