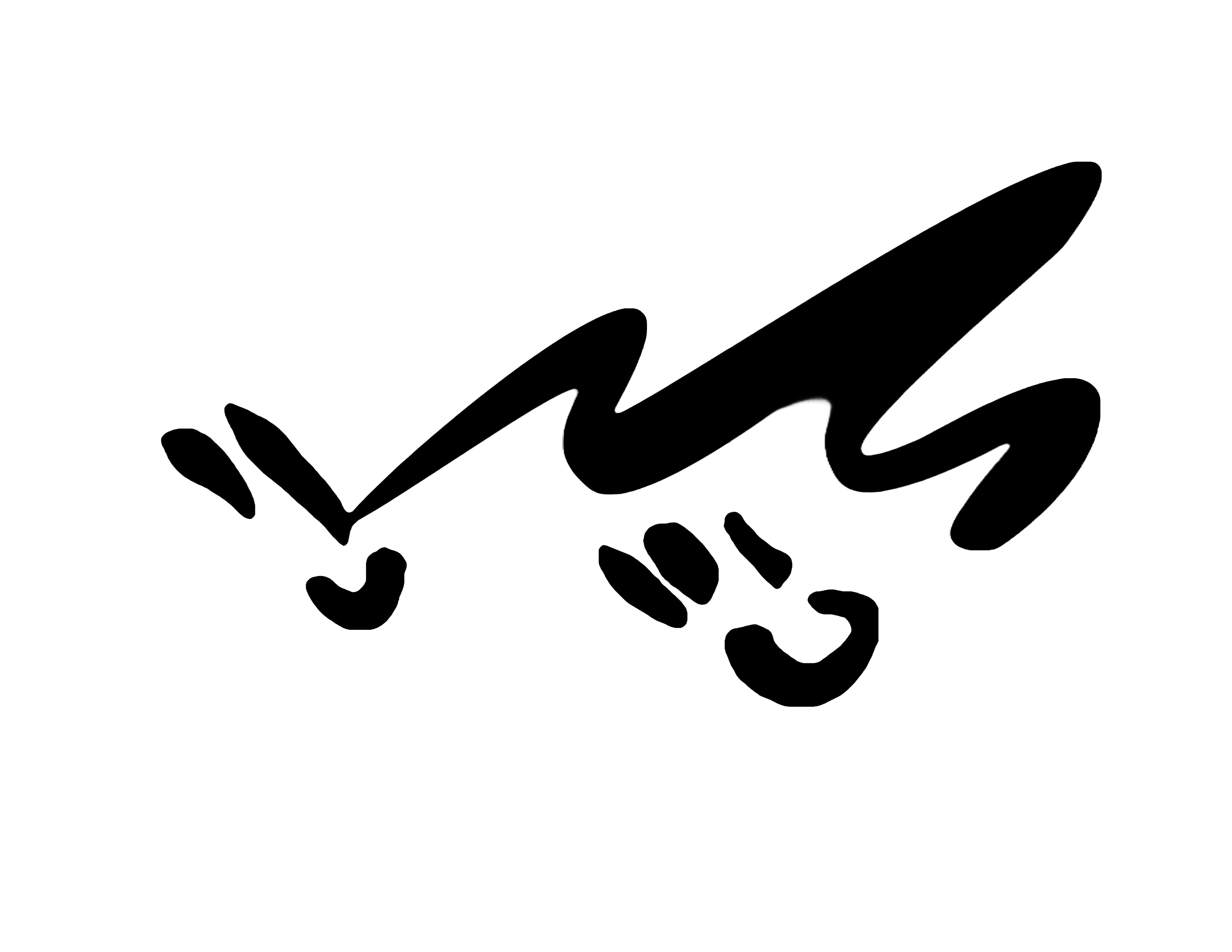《长安三万里》启发的一篇观察
blurryface

编者按:
文章试图挖掘《长安三万里》文化意象里最深沉的触动,虚实背后时代的精神状态,尤其是那些游离于主流叙事之外的视角。在一系列对历史与电影叙事本身和时代气质的解析中,作者引领我们思考,一切似乎都不仅是唐朝的盛世荣光,更是当代社会的隐忧与困境?一段由电影引发的深思,一段“把自己作为方法”的经验后记——行路难!行路难!
一个小引子:
这篇随笔现在才发出来,早已失掉实效性。就当是在一片大日历上添一小小标记,纪念2023年PEER经历的夏季日子。沅陵的暑气绵延不绝。我不敢估量在PEER挚行伴夏项目所做事情带来的影响,因为实在是自尊心大过实际行动、带来的损害或许也大过益处(即便我希望并非如此)。
所以电影只是一个冗长的引子,一个谈资,或者一个钩子。电影把我想说的话和想表达的困惑勾住,笨拙地平放。
充满愧疚地想,同学们生活一切顺利就好了,能够过得越来越幸福就再好不过了。
正文:
2023年夏天国内院线上映的《长安三万里》突破18亿票房,成为中国影史动画电影票房第二名。《长安》的爆火也伴随着许多批评的声音。有不少观众批评电影扭曲史实,编造人物特征与事件,如此如此。
种种由电影生发出来的讨论,将我引向皮毛下层的骨血——什么是历史?谁在书写历史?而当我们书写历史的时候,我们究竟在书写什么?《长安》显然是一个脱胎于历史事实的虚构故事,《长安》中的李白高适,显然是虚构人物。但,是何种程度的虚构?虚构的背后展演出怎样的真实?而“虚构”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
刻意的反差
电影最主要的叙事线索是高适和李白的对照。两个性格和行事风格截然相反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组几乎过于直白的对照。
高适是“实”,而李白是“虚”。电影刻画的高适,儿时读书不通,遭遇着类似于阅读障碍的困难;然而他遵行父亲教诲:“勤能补拙”(这四个字也正是电影通过高适本人的书写来作为高适青少年时期身心状态的一个结语)。李白的出场则飞扬跳脱,无拘无束,鲲鹏展翅一样大开大合,正像电影借高适本人之口说的:“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物”。
当然,电影是视觉的艺术,而这种”虚“与”实“的对比主要通过视觉并置呈现——电影对二人脚步的描画。年轻的李白出现在荧幕上,观众永远无法捕捉他的身体重心,于是也无从预测他的行动。这是因为他一出现、一移动,他身体的着力点总在前脚掌。二人初至江夏,登上黄鹤楼,李白醉酒吟诗,直接跳上栏杆,身体歪歪斜斜却不跌落。此时我们看不到画面下方高适的脚,而他在下方护持着李白,占据着底端相对稳重的视觉位置。这里的二人初出茅庐,李白行卷受挫,但两人还都胸怀大志,对自己的才能以及社会的上升空间都抱有期待。
彼一时,二人再到江夏已经是高适返乡多年,李白穷困潦倒而为入赘一事追赶孟浩然寻求建议。渡口追船的一幕是戏剧化的,融合了典型香港武打类型片的“跑酷”场景——李白穿越人群,跳过一艘一艘的渔船追赶孟浩然所在的帆船。他所到之处都有行人货物躲避不及而翻倒,一片狼藉。高适紧随其后,不仅要快速收拾李白造成的局面,同时需要追逐李白一同前进。李白步伐与重心的虚浮在此显露。
当然,同样的足部特写和对步伐特点的刻画还出现在别处,即高适在扬州与裴十二比武的段落。二人缠斗,一处特写打在池塘中一块碎石上,二人分别点石而过——裴十二脚尖着地,仅仅是快速地掠过了石头,而高适的一整张脚完完全全踩在石头上再而跃离,引起石块晃动,水中波纹荡漾。如果将二人脚步的特点对应回他们的此刻的心境,于是“虚”与“实”从行为模式、身体特征的对比,扩散到了二人性格甚至价值观的对比。面对高适“精忠报国”,裴十二的回应是不屑且无奈的。正如她自己所说:“青春与才华不消耗在扬州夜色与美酒美人之中,却又消耗在何处啊。”
可以说,电影在有意地通过并至一切其他角色的“虚”来映衬高适的“实”。
电影似乎试图用“虚”表现盛唐向中唐过渡的某种时代气质。这种气质弥散在社会中,从每一个社会组成部分中流淌而出。“虚”又与佛学或者老庄思想具有强关联,可以粗略地指代一种“清气上浮”的虚空状态,或者一种“无为而治”的举重若轻。
电影中的许多文人墨客浸润在“虚”的氛围中,而他们的状态和异彩纷呈的作品组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盛唐气象”。这种气象同时牵连出“硬币的另一面”——一种挥霍的、纵乐的、几乎固化的生活准则与态度。
戴锦华老师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她好友张晓红老师的一个比喻,即“前脚掌与后脚跟”分别对应着“前现代与后现代”的社会精神状态——
“因为现代文化决定了一个前倾的身体、一个对效率和速度的追求。而前现代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意味着一个有根的、后倾的、一个重心放稳的姿态。(当然这些都很粗暴。)”
虽然是比较粗暴的二分,但显然电影进行并强调着这样的二分,并试图通过这样的二分表达某种期盼,或者某种疑问。张晓红教授对于现代文化的解读当然可以扩展到当下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横行的全球化世界格局当中——个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是由且只由个人努力决定,而个人的价值体现在个人具有的生产效率——“前脚掌”这种向前冲的姿态正是这种个体决定论的贴切比喻。电影中的“虚”,以及背后支撑它的一整套社会架构成为了一面镜子,映照着电影创作者眼中“虚”的当下,和作者渴望的“实”的理想状态。
镜中风景
回到关于电影的一系列批评。与其苛责艺术作品为何偏离史实,我们不如问一些别的问题:面对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事实,电影制作者为何选择在作品中重新展现并重新串联这些事实?电影为何清醒地对历史进行改编和重写?改写后的作品具有怎样的视角?以及,改写过后,作品中的人物和时代怎样与作者本人身处的时空交叉重叠?
可以说,这部电影是由一组又一组的映照组成的。这些映照关系不仅在电影中发挥作用,也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荧幕外的世界——电影与真实世界同样构成一组映照关系。
事实上,“映照“这一行为早在电影的最开头就出现,提示着观众。屏幕上最先迎面而来一座雪山,然而几秒之后雪山的影像虚化收缩,屏幕逐渐显现出一只大鹏的瞳孔,而我们看到的映像正是大鹏眼中所见。换句话说,我们获得了大鹏的眼睛才得以观察唐代广德年间的陇右雪山。
我们听惯了“以史为鉴”的教训,可是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真的可以回溯到那个亘古不变的、恒久存在的“历史”吗?事实是,我们一定是借由某一双眼睛及其带来的视角才能观察历史。所以不如说,当我们书写历史实际上是书写当下。
电影如此开篇或许提醒了我们:历史书写本身是作为一种参照存在的;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历史的同时,我们已然不可避免地需要经由一个具体的历史对象和观察视角来探索已不可知的事实。大鹏作为某种符号——不论是它出现的时机(都是在高适追忆李白以及李白所代表的昂扬恣意的“盛世”)还是它本身负有的所谓“鲲鹏之大”的文学内涵——同样承载着观众的视角,承载着一种对过去的缅怀。
某种程度上,大鹏出现标志着高适的追忆,也同时标志着电影的起点,和观众们对“大唐”的想象的开端。大鹏眼中的映像提示着一个事实:电影中呈现的唐朝俨已成为当代中国幻想和投射的对象;“唐”,或者更广义的大唐所代表的“盛世”正标志着一种某种民族身份、民族认同的狂欢。
回到来处(吗?)
高适故事的开始和终结也同样预示着一种停滞不前的叙述进程。
年轻的高适和李白策马立于商丘的山坡上,遥望远方连绵无际的田野,登时飞奔而去,开始他的旅途。
影片的结尾同样发生在一片连绵的丘陵。此时我们知道年迈的高适还剩下两年寿命。而高适本人反而意气风发,大声呼唤着李白的名字,又策马冲下山去。此时“李白”也俨然与“大唐”和“长安”深度绑定,成为一种悬浮在中晚唐乃至现当代社会上头的符号,标志着高适记忆中那绚烂的过去。
我们的终点不期然回到了起点,仿佛兜了一个大圈子,然而停滞不前。不论如何昂首挺胸,经验如何增长,我们无法逃脱这种螺旋般的命运,始终僵驻在原地。
然而唯一不同的、也或许预示着某种新的可能性的细节是,高适身边多了他的小随从。一段生命的终点叠合到了另一段生命的起点。此时他们,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想起的是李白的这一句诗:“长安如梦里,何日是归期。”
如果目的地是长安的话,高适、年轻的随从、以及屏幕前的我们想要归向的又究竟是何处呢?究竟是未来还是过去呢?
所以说,那段“过去”,那个我们和剧中人共同追忆的过去究竟意味着什么?
更重要的是,这段“过去”对于历史中、甚至当下社会中、始终被忽略的视角到底意味着什么?
电影似乎试图撬动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叙述,牵引出一些别样的生命经验。譬如,在“精忠报国”这类由家国情怀驱使的人生价值和成功标准之下,我们看到了隐藏在“报国破敌”背后的、所谓“我们”之外的“他们”——是吐蕃、回纥、突厥,是胡人,是所谓的“少数民族”。
正如电影中高适本人慨叹:“云山城就是彼时的石堡城。”——弹尽粮绝的守城军士,无论是石堡城内的胡人还是云山城内的汉人,都是各为其主罢了。边防同样艰苦,将士们同样坚强守城不轻降,这些背后的动力或许是一些互相拒斥但并无不同的价值观念,是由领土疆界划定带来的内部认同。
“我们”与“他们”并无本质不同,只不过“我们”需要一个“他们”来确定我们自己的位置罢了。于是就连高适最终大破敌军的胜利都似乎酝酿着一个更黑暗的潜台词:此时我破敌,彼时敌破我。假如我们遵从这种零和博弈的游戏规则的话,视角决定胜败,而成败反过来稳固着我们各自的视角,强化着我们内部的自我认同。
我,唐朝的一名女子
总有人是游离在集体认同之外的。这些人不被允许加入到“我们”的建构当中来。
上野千鹤子老师在她的著作中提出“女性是一种处境”;在一场对谈当中,戴锦华教授继续挖掘这种处境的意义,以及女性处境可能牵引出的别样的生命经验和可能性。
女性处境,最直接的理解就是一名女子的处境。
电影“初到扬州”段落再明显不过地通过裴十二这个角色探索这个命题。正当高适自己纠结于自我实现以及自身困境时,电影强迫高适连同观众们一起将目光转向一直隐藏在焦点之外的裴十二。
她战胜高适几乎是理所当然的,而她脱帽露出长发揭示女儿身这一动作包含的无奈与自嘲也自然而然与她父亲裴将军本人的不得志相互勾连。此时此刻,我们终于从男人们壮志难酬的叙事中逃逸,认识了一位女子,以及这位女子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裴十二与高适面临的困境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无论如何,历史不会书写裴十二的名字。在每一位女子出生后,她被规定成为女性,被圈定在社会价值体系之外。裴十二本人正是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而对此她明知故问——“不将金银青春挥霍在扬州,却又在何处?”
对于有才华的女子,当留给她们的路注定是“风雨杳如年”,注定是在历史中匿名,生命本来就是游离在“意义”与“非意义”之间的。
在我看来,裴十二并不是唯一一个女性的视角。事实上,在裴十二斗武并揭示身份的段落之前,扬州抢歌女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歌女这一角色也在裴十二身份揭秘之后与她构成了有机互文,即,应对父权的两种方法、一体两面:一种利用自己的女性身份(或者化用铃木凉美的“情色资本”),另一种则逃离甚至“杀死”自己的女性身份。
抢歌女段落可以说是过于典型的情节剧/章回小说桥段,直落窠臼。貌美的女性先是像一个秘密一样被藏起来,而后适时地忽然向观察她的男性们显现她的魅力。(掀开被子美女露真容的镜头同时出现在《长安》和《封神》这两部夏日大热当中,可见男性导演与创作者真是对这个桥段情有独钟,仿佛这是他们习得的唯一一种书写女性的方式)。
歌女在船上载歌载舞的时候,俨然在周围男人以及观众面前丢失了自己的身份——她不仅成为了象征扬州“销金”乃至“纵欲”的符号,也成为了被猎奇的对象。她的身份成了她的美貌、歌喉与舞蹈,于是她也清醒地利用着自己的这些资本,维持生计。
然而,正是由于后半部分裴十二的提醒,观众们才时刻记得一个事实——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世界、这样的社会里,不存在女子生存的空间,也并不存在她们自主独立的选择。于是先前歌女的段落也披上了一层阴影。她不仅仅是我们猎奇的对象。事实上,我们的凝视投向她的时候,她也同样凝视着我们。她的主体性隐藏在她驯顺的面容之后。
这样来说,女性的处境在电影内部形成一种对冲,使电影的叙事本身——一个围绕着男性身份和男性书写的铁板一块——开始自我矛盾、松动。
天下捷径岂是为寒门弟子所开
回溯“女性是一种处境”这一表述的源头时,我们会回到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表述的延续:女性不是生而为女性的。换言之,用戴锦华教授的话说:
“我们今天用性别的和高度自然化的、客观的方法来描述的男性和女性。这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从来都是一个文化的规定,都是一个想象,都是一个等级阶序,而在这个等级阶序当中女性就是处在较低的位置上。我想当我们说女性是一种处境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说女性不是一种真实、一种实体、一种实存。”
女性处境包含的是一种弱势的处境,是一种属于少数群体的、处于权利下位的处境。这些人不被邀请参与到重大的社会决策当中;上升通道向她们关闭,于是她们自身的自我实现也无从谈起。
这或许不仅指射女性,也同样指射“寒门弟子”——正如电影中角色程元振指出:“天下捷径又岂是为寒门弟子所开。”我们的目光不仅投向裴十二的嗟叹“一个女子的才华“,也投向行卷无门的高适,科考不成的杜甫,以及受制于商人之子身份而四处碰壁的李白。
他们的困难当然与同时代女性所面临的不可同日而语,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共同的遭遇何尝不是一种当代中国的映射。
譬如上文,回溯历史和重新书写本质是在解读当下,是隔着时空距离来审视近在眼前的问题,也是借助遥远的身体与故事书写当下的经验。
当下正是布尔迪厄所描述的一个教育资本化的世界,一个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父权制交媾合谋的世界。个体的成败很多时候被彻底地归因于个体自身作出的选择,而有关地缘、阶级、资本、民族、性别而产生的历史性不平等被有意地弱化,被移至幕后。
当我们的教育和考试制度正在系统化地抛弃占全国教育对象绝大多数的县中学生、当国内各大高校的农村学生占比从大半数降低到不到一成,我们不难理解为何电影着如此多笔墨书写关于大唐应试、制举、行卷的制度,以及文人们如何挣扎着出人头地建立功业,而又如何地失意潦倒。
面对这样的现状,戴锦华教授发问:
“我们有没有一个不同的模板,我们有没有一种不同的价值,我们要不要在这样一个男权的也是现代主义的、竞争的、获胜的、卓越的逻辑当中走下去?”
电影中李白的“全盛时刻”或许就是他终于如愿入仕,成为翰林学士的时候。我们当然也知道,他并未如愿。
电影对这个片段对描绘具有清晰的自反视角。当来往游人仰头望着高处弹琵琶即兴作诗的李白,他们看到的是——正如一位客人兴奋地指出——“李白又会作诗,有胡人血统,还这么出名,我们大唐真是海纳百川啊!”可见,那些凤毛麟角的能冲出阶级桎梏的人们,他们所取得的胜利被社会系统收编,融合到了所谓“大唐盛象”的背景板之中,化为众多象征符号的一个。
镜中我自己
2023年的暑假,在参加国内教育公益组织PEER的暑期项目时,我有幸去到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官庄镇的一所中学举办一场夏令营。一个月的暑期项目让我明白,我真的无法带给学生任何事,反而是他们带给我的身体经验令我受益。记得前期培训的夜里,我和公益组织创始人们吃夜宵。我们从疫情的封锁谈到PEER近二十年来的演变与坎坷。
那时候《长安三万里》刚刚上映,我们便谈到观后感,谈及最喜欢的诗歌段落。
CY说她最喜欢结尾“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释然。她或许是在讲她自己的渴望与遗憾。或许释然的感觉对于她当下的一种渴求,一种未完成的遗憾,又或者说是一种希望?
而LH说他喜欢相扑。相扑的段落是另一条串联电影的线索。李白擅长相扑,并在结识高适之后倾囊相授。于是“相扑”这一线索草蛇灰线,在结尾终于显露:高适大破云山城的智计正是延续了李白经由相扑传授的一种“骗术”的奥义——“连你自己都以为是真的”。
当李白面向电影镜头,也就是观众们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暮然发觉,我们被骗了。电影对历史的书写当然是一种“骗术”,然而反观之,历史书写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骗术?
到底是什么骗过了我们?
电影本身攻克了自己。它在与“史实”分离的时刻显现出幕后的面目,这仿佛是制作者对观众的一种挑逗、激刺、引诱、挑战。什么骗过了我们?谁击败了谁?又或许,战胜逻辑本身又是一种欺骗?对李白/高适以及其代表的价值品质的二元划分是否也是一种欺骗?那么欺骗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此时的LH已经和团队一起经营了PEER二十多年。二十多年见证了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与转变,也见证着学生群体画像的演变。我们当然都知道教育公益所做的事情是重要的,如同在四面不透风的墙中开一道口子。可是变革还是从未到来,谁都很难衡量公益组织带来的实际改变究竟有多大规模。公益者一遍又一遍地质问自己:真正的改变有什么?在当下教育的“上层建筑”之下,还能做些什么?
电影的局限在于,它仍然延续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脉络——它对高适、乃至对“后脚跟”所代表的品格价值的偏爱,无疑是一种固步自封,兜兜转转回到原地,回到了这个由父权制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骗局之中。
高适对李白的追忆,即“后脚跟”对于“前脚掌”所代表的飞扬跳脱的品质的仰望,在电影的叙述视角中发生了颠倒——实际的重心在“后脚跟”,在高适所代表的当下。实际的主人公是高适,是“后脚跟”。制作者以及观众最终的落点在高适,也在高适所代表的一系列所谓“脚踏实地”的品质。这种品质又通过诗文与“儒家思想”挂钩,深度粘合。于是,不管是电影中的角色高适,还是荧幕前的观众,所有人陷入了一种对“绚烂过去”的追思。
因此,在电影的结局中(我们忘掉唐朝即将由盛转衰),“后脚跟”终于与“前脚掌”达成和解,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以诗歌和文字为载体,给电影中的文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可是,过去并非绚烂。
我们从电影中的很多片段能够得知,盛况不过是一小部分人的盛况,是令帝王和掌权者们喜形于色的盛况。崇高的志向、“大鹏一日乘风起”那般的远大目标,是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围绕着家国叙事展开的一系列图景,而影片自身也处处在提点这一图景的虚无。于是电影陷入了纠结的境地、一个自相矛盾的泥沼。究竟是追忆、缅怀过去,还是批评过去?过去究竟是什么?是“前脚掌”还是“后脚跟”?我们究竟想要什么?
我没有答案,正如PEER暑期项目结束、我与同学们告别的时候一样手足无措,歉疚万分。仅此纪念2023年的夏天,纪念同学们带给我的无比珍贵的经验。

NEXT: 曼哈顿岛所有土地已售空
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