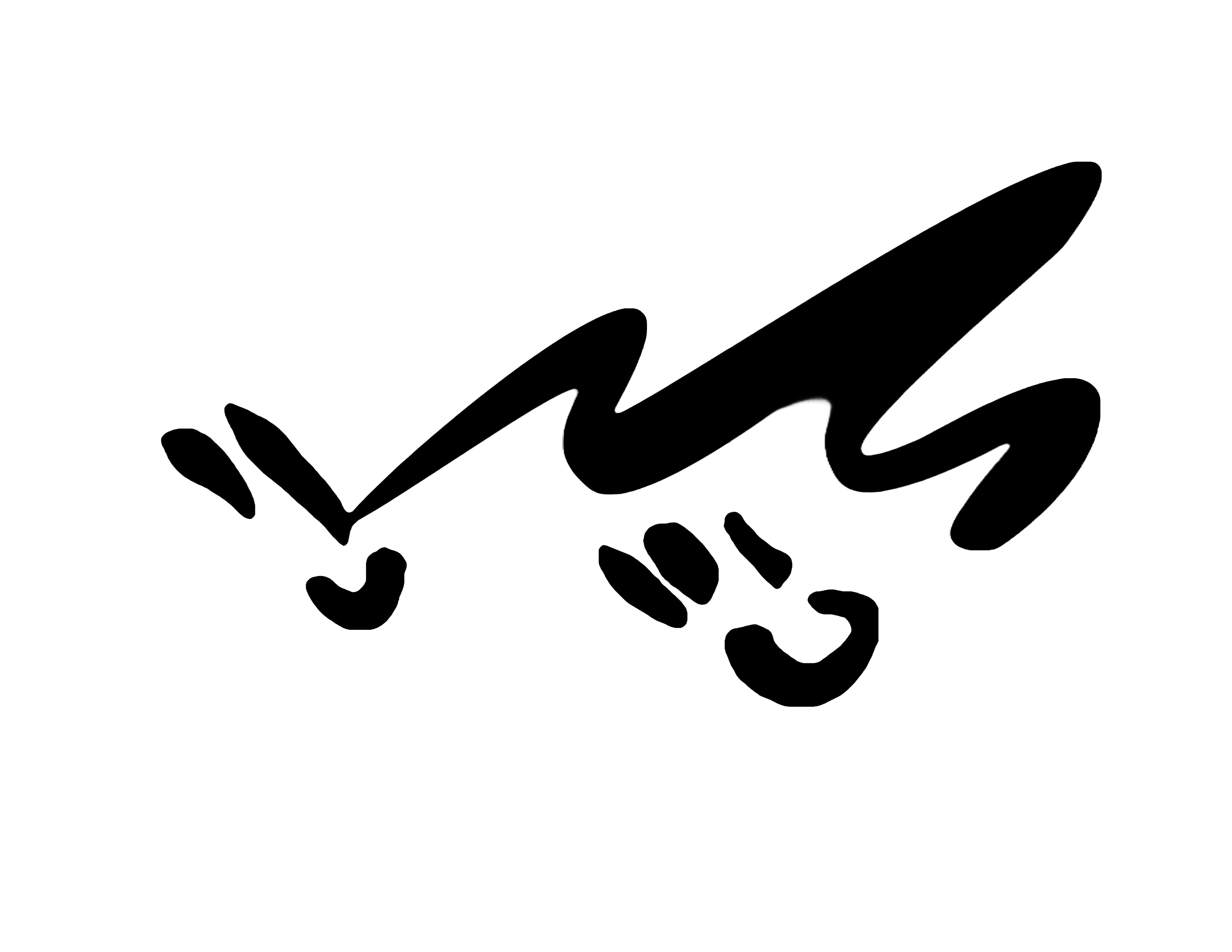美国大学抗议活
动中的留学生们
采访 文远/雷子/小水
文 麦芬

今年4月以来,世界范围内围绕着巴以战争展开的抗议活动再次迎来了一波高潮。在左翼文化尤为盛行的美国大学校园内,学生们采用占营(encampment)等方式表达自己对以色列暴行的不满与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同情。2024年5月15日,我们采访了三位身处抗议活动中的美国留学生,以下是ta们的经历、感受与观点。
2024年10月4日发刊时,距离采访也已经过去5个月时间。期间更多国家相继被卷入了这场人道主义灾难。
目录:
一、“事件已经上升到一个你很难去远观的程度了”
二、占营中的和平与冲突——理想主义如何应对警棍?
三、抗议活动中的留学生们——我们应当“一心只读圣贤书”吗?
四、抗议活动的精英捕获——我们是否过于关注精英美国大学的学生们,而忽视了加沙人民本身?
一、“事件已经上升到一个你很难去远观的程度了”
文远是一名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该校的抗议活动处于全美范围内声势最浩大之列,而今年4月纽约警方在校方请求下进场逮捕抗议学生的行径则彻底引爆了舆论——随后,各地学生纷纷以占营及其他方式声援哥大的学生。
不过,早在2023年10月抗议活动刚刚开始之际,文远并未感到十分惊奇。
“当时我们学校的几个组织在校图书馆门口的草地上抗议,我也去了几次。我开始并不是感到特别稀奇,因为我在21、22 年的时候也参与过我们学校研究生工会的罢工。ta们的一些传统、会喊的一些口号,甚至于ta们组织的形式都是我较为熟悉的。” 文远说。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文远能很清晰地感受到抗议活动在各个维度上的升级。4月17日,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开始了占营活动。几百名学生聚集在学校南草坪上,扎起一顶顶帐篷,哀悼在战火中逝去的人们,并敦促校方将投资撤出与以色列有紧密联系的公司。文远虽未亲身参与占营,但有许多朋友投入其中的她经常会前往营地找寻她熟识的人,有时也带来一些营地所需的物资。“我能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这个事规模非常大,而且它越变越大。”文远说。
§
作为一名刚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大一新生,原本对巴以问题所知甚少的雷子同样在某个时间点意识到,抗议活动已经大到不由得任何人视而不见的地步了。哥大的营地位于图书馆门口,正好处于雷子从宿舍去食堂吃饭的必经之路上。
“只是感觉(抗议活动)对我们的影响确实不可避免。当然并不是说我想避免抗议人群,我实际上也是想看的。”雷子这样告诉我们。
雷子记得,在抗议活动最如火如荼的十几天里,他和同学们主要在上课与备考期末,但同时也每天都在收听哥大的学生电台——WKCR对于抗议事件的24小时报道。他把电台报道作为生活的背景音乐,做任何事情时都在听。后来,考虑到局势的动荡,几乎所有教授都把期末考试改为选做,或是直接取消了,所以他和同学们不用再专注于学习了。
二、占营中的和平与冲突——理想主义如何应对警棍?
与中文互联网媒体常常强调的“混乱”与“无序”不同,在文远的亲身体验中,占营活动的整体基调是和平的,还带有许多理想主义的色彩。她有朋友将营地描述为一个“另类社会”(alternative society):在这片自成一派的空间里,人们因为一个共同的愿景自愿集聚在一起,脱离了外界的评价体系,共享物资,各取所需,与背景里的哥大校园与纽约市形成了鲜明对比。参与者在营地里拉起了横幅,将这片短暂逃离了既有秩序的小小飞地称为“解放区”(liberated zone)。
§
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小水也大体印证了这一点。他告诉我们,加州的第一波大型抗议发生在2023年10月末的湾区:旧金山爆发了大型游行活动,约几千人站满了一整条街,而伯克利和奥克兰等地也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游行。小水参加了其中的数次游行,据他描述,其内容“主要是举个牌子走一圈,都是和平的,没有任何冲突和口号。”
进入4月,伯克利学生同样发起了占营活动,其核心主要由各种反战组织、左翼组织构成。小水有很多朋友参与了这些组织,所以很自然地,他“基本上天天往占营的现场跑。”他告诉我们,伯克利的占营活动之烈度相对哥大较低,也没有出现强制清场一类的事件,所以整体上比较和平。
聊到抗议活动时,社会学专业的小水引用了“集体欢腾”的概念。“集体欢腾”一词多见于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的著作中,其主要含义为,当一个人数较多的集体在同一时间以同一目标为前提做出同样的行动时,身处其中的个体会感受到一种超出其本身的崇高感。
小水在示威游行的过程中切身体会到了这一点:“可能作为一个非巴勒斯坦人,我本人的感受还不是那么深刻,但是我可以感觉到很多人把这个活动当作一种集体的哀悼仪式。”在伯克利的抗议活动中,演讲者有时会在发言之前留出三到五分钟用于集体默哀,先是穆斯林的祈祷仪式,然后是基督教的仪式,旨在表达对加沙死难者的悼念。
讲到这里,小水又迅速补充道,抗议活动固然有着强烈的哀悼色彩,却也兼具欢快的一面。美国各高校的占营活动在一方面是一场悼念仪式,屠杀与死难的沉重话题为全场染上了一层肃穆的氛围;但在另一方面,它其实也是一次寄托着年轻学生们理想的实验,试图创造出一片具有解放性的、不乏欢乐的空间。人们在营地里唱歌、跳舞、野餐、读书、演讲、创作,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运动。这副胜似郊游的景象或许会让一些人质疑这一活动的政治性和严肃性,但包括小水在内的许多人并不这样认为。
“我觉得这两个其实不矛盾,政治活动也可以欢乐一点,没有问题。”小水说。
§
然而,在美国的另一端,纽约警方的进场暂时中止了这一派景象。4月18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内马特·沙菲克的授权下,警方人员身着防暴装备进场,在清缴营地的同时逮捕了超过100名学生。虽然被逮捕的学生几小时后即被释放,这一事件依然昭示着,更剧烈的冲突即将到来。
在4月18日警方第一次入场时,雷子正好在离营地不远的地方上课。课上,一直在刷社交媒体的他第一时间得到了警察入校的消息。雷子一开始在关注着现场直播,随后按捺不住自己的关切,干脆决定走出教室,亲身前往事件现场。
下午1点多时,雷子来到了营地所在的草坪旁,彼时纽约警察已经把帐篷里的学生都带走了,而校警正忙着收缴帐篷。那些帐篷随后被堆到一栋宿舍楼下,供学生去认领。草坪旁围着成百上千人,不住地谈论警方与校方的行径。
雷子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感受:“当时站在那里我就觉得挺震撼的,因为第一次在校园里看到这么多的NYPD(纽约警察)。这个事情让我对于校园的感受瞬间就变掉了,因为之前会感觉这个校园是属于学生的,但是看到那么多 NYPD 站在那个草坪上,就会有一种自己的地盘被别人侵犯的感觉。”
在警方进场后,学生们的反应可以用群情激愤来形容。即便是之前没有参与抗议活动的人,大多也在指责学校的做法。显而易见,校方和警方的行动并未能压下抗议运动的浪潮,反而有些火上浇油的意味。警方离开后,学生们迅速重返了营地所在的草坪,坐在毡布上继续占营。三天后,一朵朵帐篷又重新盛开在了营地里。
4月29日,哥伦比亚大学校方与抗议群体的谈判以校方拒绝学生们的撤资诉求而告终。随后,在其校内大学的抗议活动达到了顶峰。4月30日凌晨,部分抗议者砸碎玻璃,进入并占领了汉密尔顿楼(Hamilton Hall),同时以杂物封锁了大楼的入口,拒绝任何非抗议者进入。
在1968年4月,哥大学生曾因校方与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IDA)的秘密合作发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占领了汉密尔顿楼。自此,占领汉密尔顿楼成为了精神图腾一般的存在。五十六年后的又一个四月,学生们再次涌入了同一栋大楼,以示ta们对哥大学运传统的致敬与对反抗精神的延续。
§
抗议活动期间,文远的住所离学校十分之近,仅仅隔了一条街的距离。但由于占领汉密尔顿楼事件发生在凌晨,她直到清晨醒来后才从学生媒体上获知这个消息。
文远说,她的第一反应是:“这(占领汉密尔顿楼)是个很糟糕的主意(such a bad idea)。”她担心此举会进一步激化与警方的冲突。
当时的文远已经做好了接下来几天不眠不休的准备,无论是去抗议还是以其他方式反抗。她知道,学校一定会再次报警——校长甚至曾以国民警卫队的入场相威胁。4月30日晚,一个离五一劳动节咫尺之遥的时间点上,文远在校园的其中一个入口处参与抗议。这场小型抗议活动是自发的,抗议者们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对往来的警车叫骂。文远眼睁睁地看着一辆体型庞大、窗户全部涂黑的警车驶入又驶出现场,外观有些像一辆校巴。这时她知道,警察一定已经开始抓人了。事后,她听说警车当天驶出时装满了被逮捕的学生。不久后,她和其他抗议者得到了消息:据内部线人所言,ta们很可能会被逮捕。随后,ta们往后退了两三条街。
§
抗议者们占领汉密尔顿楼时,雷子已经在回国的飞机上了。他在飞机上连着 WiFi,通过哥大学生电台时刻关注事件的进展。校方在29日曾发邮件勒令学生在当天下午2点前离开草坪,否则将面临停学及其他“严重后果”,但抗议者们投票决定继续留在占营处。雷子认为,抗议者之所以会去占领汉密尔顿楼,很可能是因为ta们预见到了警察当晚无论如何都会入校驱赶人群:“我觉得ta们可能就是破罐子破摔——既然反正都要被抓了,那还不如做一件更进一步的事情。”雷子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主意,而是学生们在最后关头的奋力一搏,试图利用汉密尔顿楼的象征意义让整个事件的关注度再上一个台阶。
三、抗议活动中的留学生们——我们应当“一心只读圣贤书”吗?
比起美国本土学生来,中国留学生们在接触抗议活动——或者说,一切带有政治性的运动——时,似乎有着更多需要顾虑的因素。这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来自国内亲朋好友的评判与担忧。本就难以逾越的文化、语境与价值的隔阂又经过媒体放大、扭曲,于是无力与失语便成了留学生们在试图向家人朋友们解释这一切时的真实感受。
在抗议活动期间,文远的父亲和几个平时基本不交流的亲戚都在不停的给她发送ta们在小视频上面看到的各种“哥大乱象”,进行某种评论或告诫。这时,文远的回复方式往往是告诉ta们不用担心,她是来好好学习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不会参与任何此类政治活动。
然而,文远有时也会陷入矛盾当中,因为以上远非她的真实想法。她内心里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参与事关社会正义的运动是她作为一个拥有许多特权的知识精英的责任。历史专业的文远主攻20世纪近代史,在她看来,学过了许许多多塑造了我们今日所见之世界的历史脉络之后,再让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不切实际的。”她表示,自己打算在回国之后跟家人“开诚布公地好好聊一下这个事。”
无独有偶,雷子同样要时刻安抚担忧的父母。身处国内的雷子父母从各类媒体,尤其是自媒体上看到了许多针对抗议事件夸张、错误的描述,打心底里担心着雷子的安全。每过一两个小时,雷子就需要给ta们发送一条消息,简要告知ta们大学内的实时状况,再三强调自己很安全。
不过,雷子的父母也有相当开明的一面。ta们虽然会担心,但是并不会在雷子身上强加任何“不能出宿舍”或“好好准备期末”一类的限制(当然,或许有一部分原因是即便限制也没有用)。ta们会告诉雷子,只要你考虑清楚,自己能够承担后果,一切就随便你。雷子说,他因此很感谢他的父母,而在ta们这样说了之后,他也会更放心地将发生的事件如实转达给ta们。
当然,毫不意外的是,许多中国家长依然希望自己的孩子离抗议活动越远越好,最好一心专注于学业与工作。在小水看来,这种家长的想法不能被单纯地理解为中美间文化与价值观的不同,因为许多美国家长也抱持着同样的想法。他认为,这是一种伴生于特定代际与阶级的意识形态——无论是能送孩子来留学的中国家长,还是能送孩子进入精英大学的美国家长,其大多数都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高层,那么自然也会有符合其阶层的观念。
在中国,这一代人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市场化大潮。政治上,ta们普遍抱有去政治化的态度,不认同各类左翼思潮——虽然去政治化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化;经济上,ta们普遍认同资本主义秩序,以物质财富与社会地位为追求目标,而教育本身也是实现这二者的一种手段。用小水的话说,“这是一种非常庸俗的中间阶层的伦理,但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结果。”在美国,这些家长或许正是几十年前参与过政治运动的学生,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阶级的再生产与新自由主义的大行其道,ta们也开始将学生运动定性为一种年轻人的幼稚行为,会随着时间自然褪去。
“这是一种既得利益者的话术。往往告诫你不要被别人当枪使的,恰恰就是手里有枪的那种人。”小水这样总结。
除了国内亲友们的看法,留学生们自己对于抗议活动的感受与态度同样值得深究。可以肯定的是,留子们的态度绝不能被简单地归纳为“支持”,“反对”或“事不关己”——大体上,持以上三种态度者皆有之,而在背后驱动着这些态度的文化、阶级、意识形态等因素则更有探讨价值。
文远认为,她接触过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都把好好读书当作自己的第一要务,因而对抗议活动敬而远之。这或许也是最符合大多数中国人价值观的态度:我家里人辛辛苦苦、砸锅卖铁送我来美国读书,是为了让我出人头地、过上更好的生活,我没有任何参与抗议活动的责任与必要。这一态度也和上述普遍流行于中国家长间的“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心态遥相呼应。
讲到这里,文远提起了2021年芝加哥大学的一名中国留学生被枪杀后,芝大的同学们所发起的集会活动。集会中,留学生们指责校方与政府无法保障学生人身安全,要求增强警力,同时打出了这样的标语:“我们是来这里学习的,不是来送死的(we are here to learn, not to die)。”
留学生们保障自己人身安全的愿望固然合理之至,但ta们采用的标语及增加警力的诉求也侧面反映了流行于中国留学生间的某种特定思维模式。事实上,芝加哥大学周边街区的乱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种名为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的现象导致的,而这一现象正是大学与政府自己一手造成的:大学与政府合作,低价买入大量原本属于居民的楼盘与地产,变相逼迫穷人与少数族裔集中到一部分条件恶劣、缺少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街区。文远认为,芝大的留学生们并未考量到治安问题的根源,也没有意识到,增加警力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
无可否认,从现实层面来讲,(美国大学的)国际生们参与抗议活动的成本与风险要高得多。如果一个国际学生因参与抗议活动被逮捕,ta面临的后果相较于本土学生要更为严重,甚至可能危及到签证与合法居留权。很多参与抗议的美国学生也了解这一点,因此会让国际生不要上前线或做其他危险较大的事情,而是从事支援类的工作。
雷子的文学教授出身于一个低收入家庭,是家族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在抗议活动刚开始时,这位教授曾给全班发送过一封邮件。邮件中,她提醒来自其他国家、家庭较为贫困,或在其他方面属于弱势群体的学生在参与抗议时尤其要小心谨慎,因为她深知人们在风险面前并不平等。
“对于拿着F1(学生签证)的人来说,可能ta们也很想上草坪,但是出于现实考虑,可能就是没法上去,那么在社交媒体上转发或和身边人交流也是一种很有帮助的参与方式。”雷子这样说。
而对抗议活动较为支持,甚至全身心投入其中的留学生也不在少数。或许有人会认为,美国政府全力支持以色列,从而对加沙惨案也难辞其咎,因此美国人负有发声抗议的道德义务,但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没有任何责任。
然而,超越了国族叙事的普世价值观依旧驱动着许多留学生奔走呼喊。
文远更愿意从反对全球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秩序的视角来看待抗议活动。她认为,这件事不仅仅关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无论是美国、日本、墨西哥还是欧洲,都有人愿意为加沙人民所承受的苦难挺身而出。这是因为人们意识到,不公正的国际社会秩序在同等地压迫着我们所有人。只要这种秩序还存在一天,加沙人的惨剧就有可能在任何地方上演。
“不能说我是中国人、我根正苗红,我就没有这个责任了。”文远这种作为知识精英的自觉与责任感恰恰是她难以向父母解释的。
在探讨这个问题时,雷子引用了那句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没有人能够自由,直到所有人都自由为止(Nobody is free until everyone is free)。”雷子坦诚地表示,由于此前未曾接触过巴以问题,他对此并没有太强烈的情感体验。但哥大的行径让他看到了校方对于学生言论自由的打压。他认为,如果他在事件中负有任何责任,那一定是去反抗来自权力的压迫。
小水则强调,我们不能首先把自己的身份设定为一个中国人,并依此判断该做或不该做什么事情。在国族与民族身份之前,我们首先是个不加任何限定的人——当我们看到那些发生在加沙的赤裸裸的屠杀、饥饿与灾难时,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会自然而直接地告诉我们,这是错误的。他不想把参与抗议活动称为一种“世界公民的责任”,因为“责任”一词牵涉到某些政治实体的框架与规则,而“世界公民”在实然上只能指涉极少一部分在多个国家或地区居住过的精英。小水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很简单:既然他有这个能力和权力去做些什么,那为什么不去呢?
四、抗议活动的精英捕获——我们是否过于关注精英美国大学的学生们,而忽视了加沙人民本身?
本次发生在美国高校的抗议活动最常面临的指责是,其重心似乎已经偏移了巴以冲突本身,而转移到了精英大学的学生与政府和校方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上。
可以说,在当今不平等的世界秩序下,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本就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关注,而本应使得加沙人被看到的抗议活动似乎再次强化了这一结构,由此形成了一个似然的悖论——要呼吁人们关注加沙的现状,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抗议群体就需要取得足够大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同时又基于这些群体自身的特权(privilege),很容易将舆论的注意力吸引到抗议群体本身上来。事实上,本文也可以被视作以上悖论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最该关注的是巴以冲突本身,但却依然因为要借助留学生这一话题所能吸引的关注度而选择了聚焦于抗议活动中的留学生们。
面对以上指责,一种常见的回应方式是,即便抗议者们的确利用了自己基于国家、种族、家庭经济地位等因素的特权,但倘若结果确实有利于提升人们对于巴以问题的关注度,那么这样做便至少不是错误的。一个美国常春藤大学的学生与一个加沙难民在其所能获得的资源方面固然有极大的不平等,但基于这种不平等已经存在的前提下,利用不平等去消灭不平等是进步人士的最优选项。
在哥大的占营活动刚开始时,活动背后的几个学生组织曾做过一张广为流传的图片。图片的左右两边分别是1968年与2024年哥大的抗议活动,两边均强调了写有“解放区”字样的横幅,以示激进性的代代传承。甚至哥大官方都以学运传统与进步性自我标榜、宣传——可谓与其报警逮捕学生的行为形成了鲜明而讽刺的对比。
文远本人对上述现象十分反感,因为它实质上是将“激进性”或“学运”当成了一种可以被拿来沾沾自喜的文化符号:学校与学生光鲜亮丽的精英履历上又多镀了一层金,然而这种激进原本所指向的目标却被遮蔽了。
然而,从行动策略的角度来讲,她却也认为社会舆论对学生运动的聚焦是个很好的机会——一个允许左翼人士争取中间派支持与同情的机会。即便是在日益极化的美国,政治光谱上的绝大多数人也会同情被捕的学生,由此成为了一股可以被左翼用于进一步推进部分政治议题(如撤资)的力量。因此,文远认为哥大4月以来的占营活动总体而言是较为成功的,因为它确实让许多原本在政治上不甚活跃的人通过注意美国大学生而开始关注巴以问题。
小水则从被压迫群体内部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事实上,即便是在抗议学生内部也存在相当的不平等——例如,纽约城市学院(City College of New York)同样有许多学生被警察逮捕,且经受的暴力比哥大学生更甚。然而,因为该校是一所面向社区的大学,有更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及有色人种,它的学生被捕所引起的社会反响远逊于哥大。小水提醒我们,即便是在历史上的各个被压迫群体中,也往往是权力较大、影响力较强的人更有可能成功地领导反抗运动——举例来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出身于中农、富农或者甚至是地主家庭的领导人。
雷子补充道,抗议学生团体内部也经常在精英捕获的问题上自我警醒。他告诉我们,哥大的一个学生组织,哥大巴勒斯坦正义促进会(Columbia Students for Justice in Palestine) ,经常会说的一句话是 “Our eyes on Gaza now instead of students(让我们现在把注意力放到加沙而不是学生上)。” ta们会刻意地提醒大家,我们做所有这些事情的初衷还是要呼吁大家关注加沙。“所以我觉得这也是ta们做得很好的一点——ta们也会时刻提醒彼此。然后ta们扎营的时候也有很多标语会说,重点是在加沙,而不是我们。”雷子说。
§
即便抗议活动的初心能够维持不变,活动本身依然面临着其他严峻的问题:如何让影响力持续下去,以及如何扩大战线,让学生运动不仅仅是学生运动。学运面临的最大挑战听上去甚至有些滑稽:一旦学生放假,抗议活动的热潮就会锐减,甚至面临存续的危机。
小水点明了团结最大公约数的必要性:“如果学生运动想要持续的话,那学生群体内部就必须进行持续性地自觉反思,不能觉得这些(活动)是我们某种优越性的体现。如果一个运动要想成功,你必须要开枝散叶,广泛地接触各种社会阶层,各种政治观点,然后尽量地寻找一个统一战线。实际上,我们虽然管这个事叫学运,但是其实有许多已经毕业或者不是学生的人参与其中。我们甚至可能不应该用学运这个词来形容整个运动,这样实际上是遮蔽了运动参与者的复杂性。”
“学生运动自己最害怕的,其实就是仅限于学生。”文远说。

NEXT: 雨季随笔
小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