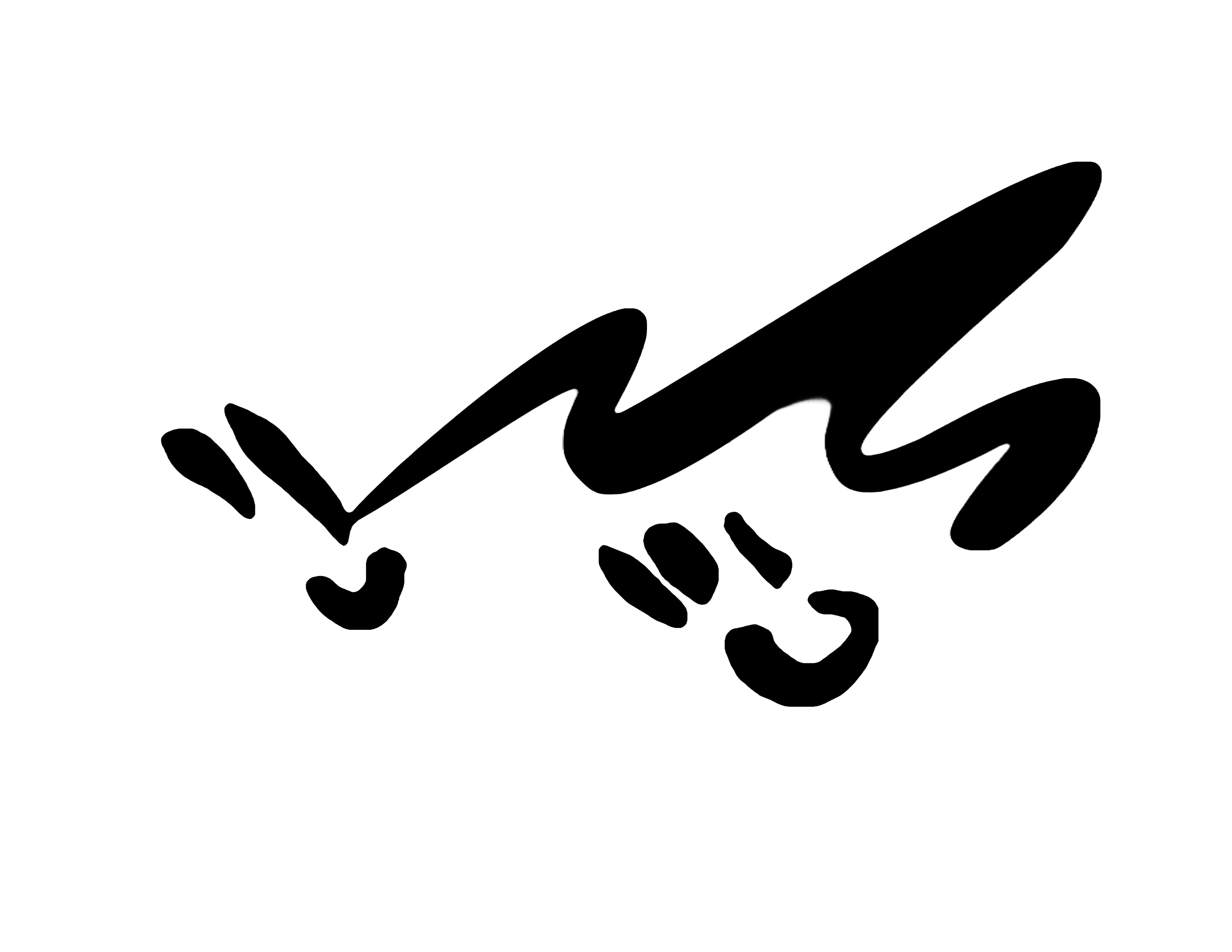“融入”美国的迷思
麦芬

编者按: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当我们于异乡刚刚步入成年,为了考试、升学、搬家、工作等等接踵而至的人生大事汲汲营营时,却在不经意间意识到,在充满机遇与困惑的留学路上,这三个哲学问题不经意间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迷思。在青春与成年,在故乡与新地,在家庭与世界,这段急剧变化的生命阶段里,我们站在数不清的边界之间,挣扎着,思考着,成长着。对于“融入”这个留学生活永恒的问题,作者由个人生活而起,谈至社会文化,历史与性别议题,以缜密的逻辑与多样的角度分享了他的哲思。对于我们而言,“融入”意味着什么?“美国”又意味着什么?相信这篇文章能够给予大家一些灵感。
一.“你有没有交到美国朋友?”
前段时间,我和我妈在打视频,我照例聊了一些选课,她照例聊了一些单位里的事。末了,她突然用一种带着三分忧心三分奇异的语气问我:你有没有交到美国朋友?
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躁突然涌了上来。我其实完全知道她想表达什么,或者说,一个从没来过美国的中国人对于“美国人”的定义是什么。但为了逼她亲口说出这个定义,我故意用一个从小接受平权教育的美国大学生的口吻说话:怎么才算“美国朋友”?我朋友里有不少人有绿卡,也有不少ABC。
她说:那能一样嘛。那肯定还是交一些本土的朋友,才更能融入当地社会嘛。
不出所料,我妈想象中的“美国朋友”,直说一点,就是白人。有趣的是,真要说本土,那她应该希望我跟原住民族裔交朋友才对,可见掌控了社会、经济、文化霸权的族群甚至可以霸占人们内心“本土”的形象,以此建立合法性。
我为我妈希望我跟白人交朋友这件事感到焦躁,同时也为我秒懂了她的意思而感到焦躁。更重要的是,我那个非常爱国、一天要提醒我三遍“你是中国人”的妈,为什么会这么在意我“融不融入”美国呢?她既希望我“融入”美国,又希望我完整保持作为中国人的自我身份认同,颇有些相类于“要求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应届生”的老中式幽默。
好吧,以善意的方式去揣度,我妈或许只是担心她的孩子无法参与一个在文化社会结构上高度异质的社群,很难通建构起一种有机链接,把握自己的主体性地位,从而陷入一种被异化了的、被凝视的处境——用人话来说,就是怕我没有在美国根深蒂固、渠道灵通的朋友,因而在异国他乡吃亏。
即便如此,我的反应依然是三个大大的问号:真的吗?为什么?凭什么?
二.真的吗?在美国生活就要有白人朋友?
当我们把问题如此直白地摆出来后,它的荒谬性便显露无疑,答案也不言而喻:当然不是!
被各种networking折磨过的我们自然不会像某些从未亲身体验过国外生活的人那样,想当然而又过度简化地认为中国社会讲关系、美国社会讲法治而不讲关系——如果硬要说,只能说两个社会中“关系”的编码和规则不大一样。但至少,就笔者个人在美国生活的经验而言,笔者很难想象去政府机关办事时会像在国内一样因为没有人脉而被刁难(可能一些来自一线城市的朋友们会说,这种情况现如今在国内也几乎绝迹了,但很遗憾的是,这在广大的县乡地区及小城市中依然屡见不鲜)。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近乎偏执地认为你总有需要医生、律师或是政府部门人员的专业意见或是内部信息的时候,而任何与你没有私人交情的人都不可靠,这也完全不构成一定要有白人朋友的理由——亚裔尤其是华裔群体里最不缺的恐怕就是医生律师了。
显然,笔者的观点不是说我们不能和白人交朋友,而是我们无论何时都不必刻意将肤色纳入私人人际来往的考量之中。坦白地讲,笔者来到美国三年,依然觉得说中文要比说英文更自然、舒服得多,依然对美式派对唯恐避之不及,乃至所有称得上交心的朋友都是中国人——可是那又如何呢?或许从某种庸俗的多元主义视角来看,没有来自不同种族、社会、文化背景的朋友是心态不够开放的体现。然而个人交友选择并不影响或伤害他人,属于私域的范畴,以道德之名对私域横加干涉恰恰违背了自由主义的核心宗旨。只要一个人可以在学业工作中和所有人融洽相处,在私交上安坐于语言、文化、习俗的舒适圈中就是一件无可指摘的事情。
三.为什么?我们的集体潜意识
既然从纯粹的实用,或者说,功利角度无法解释我们对于“和白人交朋友”这件事情的执念,那么问题恐怕更多出在心理层面。实际上,单从我们执念的对象是白人而不是黑人、原住民、拉美裔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属于心理大于实质:后三者难不成就没有白人那么“本地”吗?
几乎所有当代政治理论与批判理论均一致同意,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很大程度上作用在心理层面。换言之,我们“需要和白人交朋友才算融入美国”的集体潜意识很大程度上是几百年来白人霸权(white supremacy)与文化帝国主义的结果。正所谓“个人的就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这句话在被曲解前的本意是,许多我们认为很个人、由我们过去的经历、性格与选择所凝结成的信念、习惯与心理,实则是更宏观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的结果。
认为需要和白人交朋友,实际上是需要获得白人的认可;之所以会需要获得白人的认可,是因为我们潜意识里默认了白人对美国社会资源与最终解释权的把控。当然,从政治经济文化角度来讲,这在如今的美国依然很大程度上是事实,但要想改变这一现状,首先要做的便是从心理上拒绝接受不公正的社会安排,破除“一定要和白人交朋友”与“融入美国”的迷思。
四、凭什么?“融入”背后的社会正义议题
说到底,“融入”这个词、这套话语,本身就遮盖了许多丑陋的社会结构。我的政治教授曾说,处理社会平等与正义相关的议题时,我们总可以问出这样一个问题:谁得到了什么,以何种方式(who gets what, in which terms)?那么就“融入”这个迷思而言,我们也可以问:谁是需要“融入”别人的人?谁是只需要坐等别人来“融入”的人?“融入”是如何发生的,又有何种代价?
“融入”相关问题上的种族维度已经很清晰,在这里便不再多加赘述了。但在这一问题上,性别视角,以及性别与种族的交叉视角,同样重要。
整体而言,亚裔女性比亚裔男性更能“融入”移民目的地社会的文化与社交圈、取得的社会成就更高,笔者个人的某种“身边统计学”也吻合这个结论。但当我们提出这个现象时,随之而来各种问题就已经呼之欲出:首先,(尤其是从亚裔女性本身的生活体验出发)这个现象本身是否正确?其次,就算结论正确,亚裔女性在其中又付出了何种代价?最后,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针对第二个问题,亚裔女性所付出的代价之一或许是迎合了美国社会中基于性别和种族的刻板印象。美国主流叙事中对亚裔的刻板印象和对女性(带有男性凝视)的规训标准出现了重叠(温顺、被动、阴柔、重视家庭),因此亚裔女性被塑造成了某种“模板女性”,以一种被凝视的姿态变得“更受欢迎”。
当然,尽管亚裔女性在移民地的成就存在代价,但这整体上而言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至少就笔者个人观点而言,“亚裔女性在移民地比亚裔男性取得更高成就”本身证明了亚洲、尤其是东亚社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枷锁和压抑有多离谱。正如墨尔本大学教授马嘉兰(Fran Martin)在她的新作《远走高飞之梦:中国女性留学生在西方》一书中指出,“许多女性留学生的学历和移动性资本成了她们对抗父权家庭最重要的资源,远离父母的留学生活也使得嘉莹脱离了父权家庭、亲缘社会的监视和控制,能够做出不同于父母人生的选择”。就算有与之相对应的代价,平权文化相对盛行的移民地社会也给了她们发挥自己的活力、生命力、才能的机会,在物理意义上的他乡重新建构起一种摆脱了原有权力结构的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亚裔女性面临着一种“前狼后虎”的两难局面:退则承受母国的厌女文化,进则迎合美国人“蝴蝶夫人”式的种族性别双重凝视。与其说是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不如说是在二者之间挑一个相对而言不那么坏的。这也再次印证了一项早已为我们所知的洞见:在社会结构性不公依然根深蒂固的时代里,谈论来自受压迫群体的个人的自愿选择永远是没有意义的。

NEXT: 亚洲超市故事
青弓
wushushan9@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