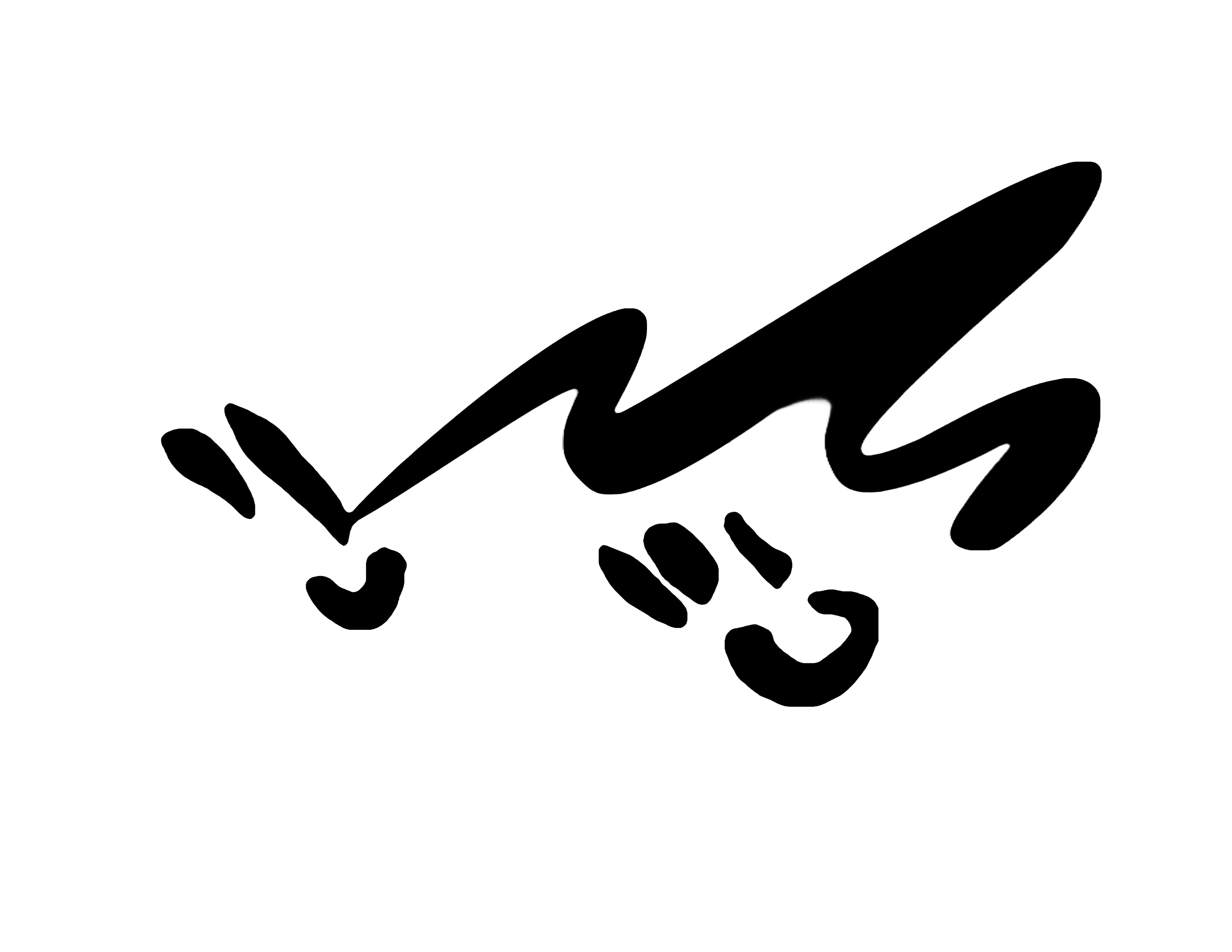雨季随笔
小帕

编者按:
“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因为此刻正有细雨落下,或曾经落下。下雨,无疑是过去发生的事。” 在一场《雨》中,年迈的博尔赫斯回想起少时曾居住的庭院,以及早已逝去的父亲遥远的声音。
雨水是亘古的隐喻。它是原始森林中滋生万物的甘霖,现代城市里唤醒混沌的风暴;是我们在胚胎中原初的养分,也是死亡时亲人最终的释怀。这种潮湿,自然,遍布一切始终的隐喻,串联起了我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游走在不同文化,地域与语言之间时的普遍羁绊: “雨到了这里缠成线,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
如此这般,作者用广州、曼谷、与清迈的雨串联起了她游离在梦境,回忆乡愁,以及崭新世界中的无垠生活的数个瞬间——“可能从天而降冰凉的水滴,就如夜里悄然而至的梦境,连同我生命中曾发生在校园和家里,那些数不清的滂沱大雨,是所有人不可译却相通的语言。”
「广州的雨」
雨下了一整天,除了我刚回家那一周,短暂地休憩了片刻——阵雨还会像久治不愈的咳嗽痒上一个多月。但我很想念广州的雨,远不像热带地区那般野蛮如千军万马之势。珠江汇入南海,其中裹满乡愁的水滴,随着亚热带季风被捎回广州,淅淅沥沥、连绵不断得就像没有解药的慢性疾病。虽然是“花城”,但广州并不是一个饱和度很高的城市,因为总是乌云密布,空气中有一层灰蒙蒙的滤镜,就连建筑也是,上了岁数的楼房,牌匾不再光鲜亮丽,而是斑驳生锈,从远处就已经散发着晒不干的霉味。旧建筑上流下了泛黄发黑的雨痕,像一条条擦不净的泪渍。
所以广州对我来说,似乎总比我去过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多愁善感。这种情绪的强度会顺着人的潜意识延续到梦中。常常下雨的地方,会长出两个世界,大海一次次游回就近的大陆,路边的水坑如汪洋一潭,反射出另一片天空,那是广州在做的梦。在梦里,陆上的哺乳动物会长出鳃与鳍,重新回到海洋。就像黄锦树在《雨》里写: “无边无际连绵的季风雨,水獭也许会再度化身为鲸。”踩进不同的梦里,水坑里的泥巴溅到小腿上,像一双双小手抓住人们的脚,再被挣脱开来。
急促的雨滴却是现实,一遍遍敲打着梦境,人对梦的记忆一圈一圈震荡开来直到平静。而雨水触碰我的皮肤,好像广州也梦见了我。
广东人湿气重,也容易做梦。在持续阴天的广州,睡前若是昏暗的,醒后也还将暗无天日,常常让人怀疑留在了梦里。很多人也许都去过不同的城市,但每个人一辈子只会在一个地方真正地做梦,不论是睡眠中还是清醒时,安稳地梦着。对梦境的偏爱,并不源于它弥足珍贵、稍瞬即逝且难以铭记,而是来自于一种信任——就像人在梦里毫不犹豫地坠落和飞翔,在这最真实的幻想当中。
但你偶尔地醒了过来,在最熟悉的街道口。雨点打在铁棚顶,炸出破碎的呓语,雾气在玻璃窗上勾勒出指尖的轮廓。伴着鼻息间缠绵的绿叶白花香,每一个曾站在这个路牌下抬眼回眸的你自己,都屏息凝神地注视着彼此。
「曼谷的雨」
自从到曼谷以来睡眠就变得很浅,半夜突然醒来又睡回去,好像总游离在睡不饱又醒不了的状态,像南洋文学里日光下,梦和现实混淆错乱。雨季如期而至,但降水量并未达到峰值,只有隐忍的风,挨家挨户敲打着挂在门前的风铃,像玻璃一块一块碎了开来。在这样的傍晚坐摩托比白天舒服,城市的热浪和潮湿的冷风交替着扑面而来,每次呼吸的下一口空气都是未知的气味。“感受异国情调的首要工具是嗅觉。”我在刘子超的书里恰好读到这句话。嗅觉是记忆中无法造假、也无法凭空再现的存在。回忆,顾名思义,是需要回头拾取的。但每次漫步在曼谷的街头上时,我才发现,原来回忆也是可以靠双腿走进去的。空气中混乱复杂的气味——烟火和食物、汽车尾气和绿植芬芳,像老旧电线杆上缠住难以解开的结,向我记忆中的揭阳家乡蛮横地进军。
在拥挤的楼群里,曼谷的天空很窄,云走得很快,而人很慢,我散步到广场里听学生乐队演奏,唱着我并不了解的语言。这实际上是场有趣的实验,在一个语言只是一知半解的国度,我可以屏蔽语义本身和延伸的含义,可以在音调通过我大脑思考前就停住,可以在我有限的想象力中组装成无数的解读,猜测那些涌动在陌生文字下的情绪。芭芭拉卡桑写道,“当我们说着不只一种语言时,会让我们免于认为自己是唯一掌握真理的人。”对于另一种陌生语言的想象,则让我持续处在对其他现实的期待和共同话语的索求中。旋律一直在空气中晃荡,直到第一个被乌云眷顾的人抬起头来伸出手,然后人们一个接一个昂首呢喃,我也望向低沉的天空以示回应,这是人与雨默契的交流方式。可能从天而降冰凉的水滴,就如夜里悄然而至的梦境,连同我生命中曾发生在校园和家里,那些数不清的滂沱大雨,是所有人不可译却相通的语言。
我又想起以前坐在车后座,在晚高峰的车流里,雨像堵不完的交通下个不停,我倚靠在车窗上看雨滴从车窗滑落,暗自地竞猜某滴雨水会在下降的赛道上勇夺头筹——于是我最期待的那颗小雨滴,会用力地跑去拥抱下一颗,再下一颗,颤颤巍巍地成为我早已内定的冠军。
「清迈的雨」
还是从最熟悉的开头动笔——对比起曼谷的雨,清迈的雨倒是有着不一样的脾性:曼谷会酝酿一整个白昼的潮湿,在傍晚淹没整座城市的喧嚣;而到了清迈,白天总会沥沥淅淅下几场太阳雨,像惬意的游客走走停停,降水在日落后反倒安分起来了。我一直默默笃信一个地方的雨蕴含着它本身的秘密和规律,现在看来确实又印证了一遍。为了庆祝这小小的得意,我在一个下雨的午后看完了《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这是好朋友提醒的,当你看了某个目的地的电影,这段旅程就会更有意思。实际上或许恰好反过来,我是因为阿彼察邦镜头下的雨林,才对清迈更加向往的。我握住这尚未流逝的,热带雨林的触感走进山林中,体验到了比大城市愈加光怪陆离的梦境。清迈什么都很低,房檐和树枝压得很低,天空也沉沉地垂下,让人昏昏欲睡。
之前我说在曼谷总少眠易醒,但到清迈这一周,我睡得特别多,好像是把我在曼谷每天不到七小时的睡眠都给补了回来。同事讲在清迈的线上工作老是容易出错,好朋友则也同意自从到了清迈就很容易困。阿彼察邦在采访里说电影就是一场梦,它们拥有着特殊的语言。电影应该跟观众对视,“打破时间和空间,在秩序中唤起不安的感觉。”梦境也同样打破再建造起某种秩序,和现实隔岸凝视。这几晚光顾了好几家当地的清吧,在几巡微醺后,我好像陷入了这种电影—梦的超然时分,我盯着不同特色鸡尾酒自己的名字,它们的故事也在我大脑里开始播放,这次酒精建立起了秩序,我意识的阀门半开半合,它就越过了我个人现实的秩序。
我又何尝不在意呢?我在意所有的细枝末节,你目光未曾落到的角落,我在意热带雨的善变,和你脸上的阴霾。歌单随机到盘尼西林的《再谈记忆》,清迈的记忆是什么呢,是蝙蝠吊在寺庙的隧道顶上;土狗和野猫伴着僧人吟诵经文;在不结束的夜里年轻人不戴头盔骑着摩托驰骋在马路上,如《青少年哪吒》里的一帧。清迈的记忆,是起伏的山脉,还有你没来得及给我的回答。
我正躺在驶往曼谷的过夜列车上,铁轨的碰撞像永不停歇的斑鸠咕咕,摇晃着我狭小的床铺一隅。冷不丁地,泰语里某个谐音梗蹦进脑子里:“电线杆”和“周六”的发音都是sao,而泰国街头的电线电缆总是杂乱无章地搭在一起,人们的星期六也常常混乱繁忙。于是我感觉,在这个周六的晚上,我身体里平白无故升起好多根电线杆,电流声滋滋作响,心灵与外界的讯号频繁交流又故障,好像逐渐远去的清迈还在对我窸窣耳语,我就要连话都表达不清了。
也许是词不达意的借口——但清迈,你是我一段无序的梦呓。
–掉落的零碎–
1.
下班后在哒叻仔闲逛,这里是曼谷最早的华人聚居区,保留了很多祠堂和寺庙,也涌现了很多新兴的艺术社群。入夜后随便走进了一家路边的餐馆,老板听到我和好朋友视频时说着普通话,她叫坐在另一个桌子上的老人递给我菜单,用普通话给我介绍菜式。下单后我邀请他坐下来聊天,我问他是泰国本地人吗,他说他和我一样,是中国人。
他已经八十多岁了,听到我也是广州人之后,用很熟练的粤语和我聊天,熟练到有时候我反而还说得有些蹩脚。但他其实解放前就搬来泰国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八岁的时候像电视剧般出来了一个父亲,带着他和妈妈坐船一路到了曼谷。他记忆里还残留着日军入侵广州的片段,但后来印象更深的是越战时期,曼谷的街道上运着军人的尸体送往机场,回到他们的故乡。留在曼谷的华人,男的就去当收数佬,九出十三归;女的就陪着唱卡拉OK。我还是很诧异他留在泰国这么久,粤语和普通话却丝毫没有生疏,我问他搬来之后有上华人学校吗?他说后来泰国发生排华事件后就不再读书了,即使在路边跟人说国语,也会被判定亲共的倾向而被逮捕。因此他的儿女从小上泰文学校,也不会说中文,在波士顿和加拿大读完书后回到了身边。他后来也回到了大陆——“现在不回了,那边的家人全都去世了,”他补充道。我在咸柠七的播客里听到一句话,“如果一个国家的地势太平了,那么它的国势可能就不太平。”这句话仿佛在泰国被很恰当地印证了。我们从他成长的故事讲到泰国近代华人的待遇再到他信和王室的新闻,我才知道周恩来总理有一个泰国华人养女,而她的生父跟很多政治家,被冠上不同的罪名,都因为亲华亲共流亡到其他的国家。
他很欣慰地说,以前曾经避而不谈的中文,现在在中学大学都成为了很热门的学科,我接过他的话茬,“泰国富豪榜前十有一半都是华人吧”,然后他指了指街对角的711,半开玩笑地说,“在711,除了棺材你什么都买得到。”(711的董事长谢国民籍贯广东澄海,为泰国首富)
2.
我对泰语里豆芽菜一般的字符一直很感兴趣,在曼谷实习的这段日子,我每天望着轻轨上音译的地名和它们的泰文书写,慢慢就把字母都认了下来。在糟糕的高峰期交通里,看着路牌发呆的时候也能试着把泰文拼读出来了。跟泰语比较起来,这个几个月断断续续学着的印尼语倒是简单多了——不需要重新适应的拉丁字母,语法清晰简单。这种为了贸易便利和民族平等重新融合的“政治”语言,总归比不断进化到现代的历史语言要便捷得多。然而在和泰文字母暧昧时期中,这些弯弯绕绕的文字就像一首首读不懂的诗,如同黄纸符箓,本就不该由我解读。但我又倔强地想通过语言这扇门窥探另一个世界。语言和语言之间既有孕育般的继承关系,又有互相碰撞粘合迸出的新火花。
最初对泰语萌生出兴趣,是因为它念起来像我家乡的潮汕话和白话,数字农作物饮食里共享着很多词汇,就像每日点头问候熟络的陌生邻居。粤语有九声六调,朋友跟我说可能正因此,粤语歌总听起来情绪丰富。泰语里的五个声调或许也如此丰富了它的文化。后来学了梵语,又发现这两种语言中的默契相通之处,知识一下相通起来。泰语里的“世界”叫โลก,念lok,源自梵语里的लोक(loka),意为“世间众生”。而暹罗的名字“Siam”则源于Krishna那黑蓝色的皮肤。
于是每当我次次朗诵出泰文,感觉总有不同的世界在我身上绽放。我一边游览着印度教-佛教文化里纷繁艳丽的庙宇,一边穿梭在市井街头分辨着熟悉的口音,炊烟袅袅如乡愁绵延。而我知道在这个,或另外语言里还藏着许多待我发掘的世界,足以让我伫立逗留上好久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