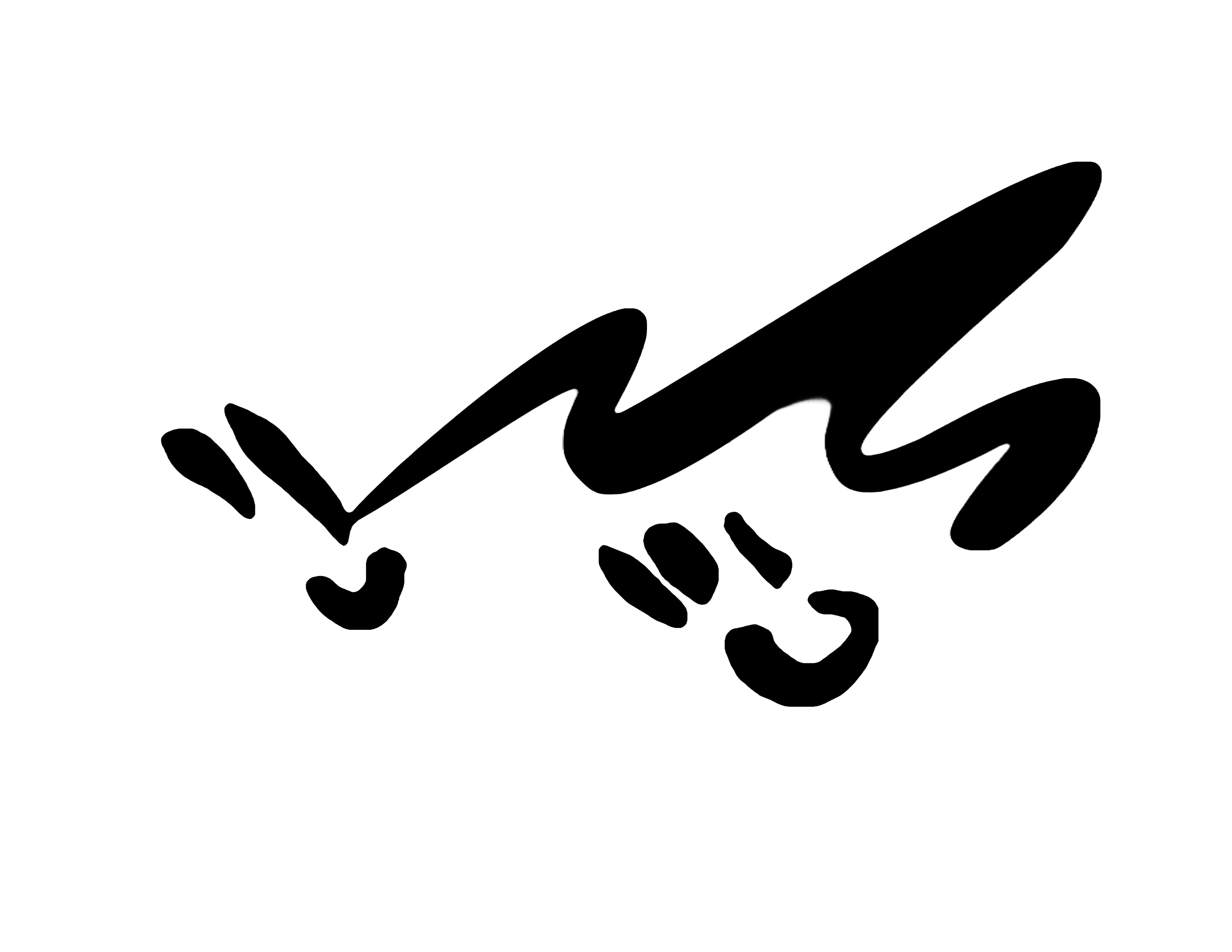萝铃的魔力、老屋
识烨

编者按
《萝铃的魔力》一诗中,作者对人的身体经验有着细致入微对体察。小孩子成长是许多事:是被扔进与他人的关系,是开始拥有秘密,是身体发生变化。这些细密幽微的心情如同热带绿植一般生长缠绕,烙在手里攥着的玩具、文字中,和故事里。在某一个瞬间,小孩可以拥有魔法,用笔,用一把虚拟的剑,刺破旧的,构筑一具新的身躯。
《老屋》有点像史诗的切面,是一整段历史中经常不被言说的部分。记忆让新的经历降生,如同母体被剖开,诞生新生儿。作者真诚到几乎令人感到疼。可是诗歌本身已经不疼了,或者说,疼并不是目的。目的是疼所带来的视角,带来的“看见”,以及那种后知后觉的浑然一体。
萝铃的魔力
——致敬陈柳环《萝铃的魔力》
睡不着,就望着天花板
想着萝铃如何获得了魔法——
桌斗里,每人揣着一把秘密
陀螺、米米卡、禁忌的糖果,男孩们飞跑
掷出一个个塑料公仔,和滚烫的词语。
脸颊红扑扑的女孩牵着我,溜出校园
到很远的图书馆。“这个好像很流行——”
第三部,没头没尾的故事,将他们的笑甩在身后:
我是长发女孩,我是密林守护者
是姐妹,是兄弟,是绿色的精灵
是端着书苍白的影子,眼镜片如年轮生长,
仰头凝望讲台,等赞美同粉笔灰一起洒满肩头。
你知道吗?我也出生在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九日——
你大概忘了我,可我记得你
化成灰我都能认出你。萝铃,
你一出生,我便替你日复一日受刑
吞下不属于我的魔法,偷来盾与剑
——哦,主角的背面,我的复仇之神。
那时女孩们刚开始窃窃私语,平坦的胸脯
隆起小小的硬核。课间,天蓝色柜子前
递去不能说的塑料包装,抻校服下摆遮住屁股
她说:魔法起源于欲望。五千年前的冬夜
寒冷之人一个闪念——要有火
美丽富饶的萧龙星球便陷入恶战。
墙上影子斑驳,发光的小人溜进卧室
沿着地板边沿走动、跳舞,哼唱儿歌
我闭眼检阅生字方阵,等太阳透过窗帘
再从被窝里爬起、刷牙,将牛奶咽下肚
走向硝烟弥漫的教室。叫他们停下,叫他们
不要再跑——对不起,伤害了你
可我必须战斗。哪怕医生和巫女
也要有一招制敌的本领。若不能挥拳
那就用笔吐出子弹——老师送的长颈鹿日记本
第一页写下:诅咒之书,黑暗之书
再画上磕磕绊绊的藤蔓,锁进衣柜——
不要哭。只要有耐心,奇迹总会降临。
“她唤醒了魔力,可她并不幸福……”
妈妈,我是女孩,我想变成鸟。在冬天
乘着野生的树枝升空。我体内也有魂魄
正日渐膨胀。当两腿间热流涌动,裸体面对镜子
开始叫我们难堪,兰花指也不再翘,萝铃
独自走入浓雾,树下的人等待已久——
布满胡须的脸呼唤我,如焦渴的狼
我喊“不要!”,那雾却一次次将我盈满——
当一千只鸟飞起,你也随它们飞去
才想起童年是场巨大的骗局
可海底不是答案,远方也不是。
“她以自己的意志昏迷,只有她自己
才能救她。”晦暗的十一岁,你第一次
踏进空教室,将沉默的花点燃
朋友,这一次我们不要躲开——
五千年前,谁不曾有过完整的身体?
创作意图
《萝铃的魔力》是我对文学最初的悸动,为我童年的惶恐、撕裂感、模糊的野心和愤怒赋予了言辞。写这首诗之前我在做一个家族史项目,采访了妹妹,听她兴奋地讲述她喜欢的《火影忍者》和《精灵宝可梦》。她用里面的人物和设定为自己创造了好几个动漫形象,每个形象都含着复杂的身世和性格特质,跟我从小到大用《萝铃的魔力》和《猫武士》给自己编故事的经历非常相似。采访中我感受到,我们总在寻找可以容纳自己生命的词句,小时候电视和书本上的故事成为我们最初的语言,而我们一遍一遍在脑海中重新讲述它们,这些故事逐渐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在与我们情感和历史的缠绕中不断变幻出新的形状——我们个人和社群的神话传说就这样诞生。当我重读自己从初中到现在的写作,我依旧可以辨认出很久很久以前在《萝铃》中习得的灵感:一个女孩有着被认为危险的魔力,在浓雾中窥见神秘的男性灵魂,跟随飞鸟到远方的小岛上寻找自己的身世——不仅是血缘意义上的家族史,也是灵魂的世代更迭,以及自己和身体内魔力强烈而矛盾的关系。
这首诗提及了很多小说里的人物和剧情,也有我自己的魔改,但我希望完全不了解这部书的读者也能看懂。我们从小接触的作品并不一样,但我相信那个驱使我们阅读、讲故事的火花是相通的。

老屋
妈妈,等到老屋不复存在,
我们背对墙席地而坐,才明白
课本里每个句子都写满背叛。
那咒语自古已有,在太姥姥的米袋里
窸窣作响,姥姥坐火车北上
踏过草原淋湿的矿堆——某一天清晨,
大姑小姑出嫁,地板和墙壁生出霉菌,
女孩长成女人。饥荒已不再,饿却不停。
我们将一知半解的词语囫囵吞下:你说脏污的血
每月流出子宫,顺着下水道落荒而逃;
我却想象不为人知的地窖里,血的叶芽
暗暗重生成森林。梦里,我的腹中打开山谷——
我起身,家族便在脚下隐隐颤动,
我用铅笔刀划向乳房,你就脊背发疼,
我破门而出,老屋的记忆便扯开大洞,
北风飞旋而至,灌进我们共同的水。
你们脚下也同样布满裂纹。
如今废墟上盖起学校,北屋的族群
落石般四散东西。粉蓝黄绿色高墙之下
孩子们歌唱铁的太阳。正午的操场无人记得
老屋地基边有个杂草丛,草的根系无始无终,
越过洗衣房、寂静的餐桌,那里埋藏着另一条血脉:
在她们离家前,你也曾蹑足于晦涩的童年,
扔下背包和字典,在白茫茫的冬夜揉搓双手。
猫为你衔来死麻雀,羽毛散落一地,
你手捧鱼骨报以回赠。当它飞跃过胡同,
你也一同起跑,唤树下鬼魂一一苏醒,
涌出没有语言的呢喃,蹦跳、摇晃、挥舞手掌,
你将熟知的名字哈入手心——
姐姐、姑姑、母亲、父亲、奶奶、姥爷——
它们随枯叶旋转、升腾,在风中汇成同一束,
字的棱角混成不可辨的鸣响——二十年后
你平躺在床,刀剖开肚腹,双手托起湿淋淋的婴儿。
那时你仍可见洁白的光由夜幕流泻,
爬上碎裂的砖瓦小山,向清冷的风敞开衣领:
雌雄同体的月亮将我们洗礼。
创作意图
去年十月份我写了这首诗的初稿,写完之后卡住了于是一直搁置,今年六月份才把它重新打捞出来。它原本的标题叫“祖咒”:那时我为自己的性别错位感到痛苦,在日记里写“……从曾祖母一辈绵延至今的诅咒,让女孩成为女人,男孩成为男人。”本来是很愤怒的话,但我不小心把“诅”写成了“祖”。由此我突然想,如果诅咒不带有恶意而只是“祖先的咒语”,这个咒语是什么样的?在课本和家谱之外,还有那些由过去绵延至今的咒语?当我重新开始创作这首诗,我发现最初驱动我的怨恨淡了很多。我不再执着于性别的咒语如何让我残缺,越来越感受到残缺只是被主流叙事压抑的身体形态,就像被城市驱赶的森林,里面奇形怪状的枝叶和根系可以撬动既有的体系,形成一种由身体内部发出的、浑厚而流动的完整。
作者介绍:识烨,2002年生于北京,喜欢听故事和讲故事,写小说和诗歌。

NEXT: 烧房子、洞
藿香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