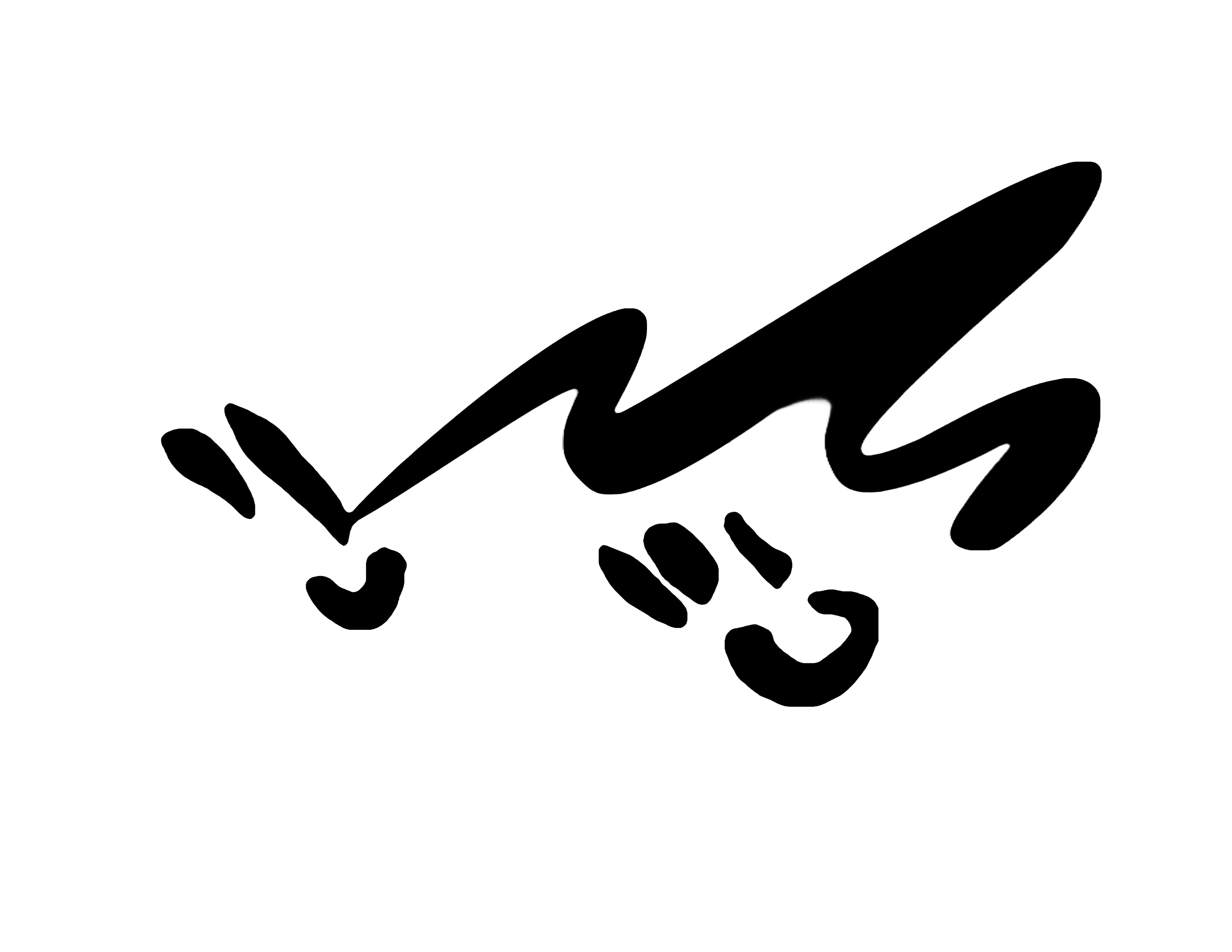烧房子、洞
藿香树

编者按
《烧房子》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在“烧”中注入了一些与愤怒有关、但不那么有指向性的情感。比起思考,“我”选择行动,借着火苗莽然不顾的热气从段落奔向段落(即便文字本身都冒着丝丝冷气),决绝地与过去分离,神色匆匆赶往下一站,前途未卜。
《洞》中的情景,常常航旅的读者们可能并不陌生——巨大的航天器被吞入云层,机舱内也模仿夜晚,将灯全部熄灭,留下乘客们做各自黑森森的梦。“我”梦中的佛像似乎是诗眼,在暗示某种答案。可是佛完全不回应任何人的祈祷。于是一遍一遍地,“我”进入洞,如同重新进入子宫、诞生——这些就是仅有的承诺。
烧房子
点一把钱,
盘一包破布,
我烧了一座房子,
和里面十岁的我。
他没有思索,
眼中连播着泡影
迈进窗外的傍晚
握住粉红的毛靴
铜钟响了,
他和鞋飞向冬天。
红墙上泼了一滩夕阳,
我烧了一个流泪的妈妈。
烧了她带着香水的围巾
和北风制成的长袍。
她冰冷的下巴
贴在我滚烫的额头。
我烧了座假山,
烧了野山移植来的梅花
土里埋着
关于阳光的记忆月牙膜。
我烧了爸爸的尸体
他的灰和爷爷的纸钱
顺着气流上升
落到原野黑暗的身体
羊群正在那儿安睡
我驶过夜空中廉价的旗子
穿过风中喃喃的旗语
重复着 这悲伤的土壤
火熄了
北京 忧伤地坐在
一片珠帘的阴影后面。
我看着我的猫,
看着我们
同样紧绷的命运
和嘴唇
然后
我
把弟弟留在那里
再匆匆地
融进这白夜
洞
我钻进洞里去
钻进一个幼稚的夜晚
没有镜子的衣柜
飞机飞过
塑料灯带和田野
频闪的航行灯
在香烟的黑风里
暗示着开始
一个充满白光的梦。
大脑的颜料
漫过洞的岩壁
炙热的额叶
碰撞过热的引擎
我向前祈祷着
那眼前的白光呀
打在我脸上
一万人的摇滚
灼烧着
额头的年轮和内心
梦的色彩
从大脑漫出来
光呀
伸手就能触摸 ——
我却被留在
十八岁的洞里
黑暗之山的佛像
看着我走进
灯光的城市
怎样才能祈祷
算出心脏的有限解
独自奔跑
就在橙色的夜里。
光趋近着极限
打在眼皮上
怎么佛只是看着
不回答呢
十八岁的我
走进陌生的夜晚
机翼的光
如雷声照进眼
就这样飞在
黑暗子宫里
等我在上一春夜出生,下一春夜死去
橙色的城市
黑色的田野
都是我的远方;我沉默地爱着你。
把全部的生命
归成爱你的目的
一种便利的说法;但却安心
做有原则的伪君子
或精神鸦片的分销者?
答应你:我会爬出洞。
创作意图
這两首詩都跟“成長”有關,分別對應著成長時不同的心理和階段。不僅是關於我的成長,同時也寓意著當代或某社會學概念上的青年群體。
《燒房子》想表達一種跟過去切割的決心。《天堂電影院》裡主角多多的爺爺告訴他,離開西西里,成為一個新的人,不要再掛念他,不要再回來。多多離開了幾十年後直到爺爺死去時才回來。那時他已是一個不一樣的人。第一次看這部電影正是我離家去上大學前的暑假。之後,父母在我的心中就已經死了,成了沒有家的人。我選擇了與我的家庭切割,不是因為父母是很糟糕的人,而是渴望真正的成長和觀念上的轉變。
《洞》是今年我坐飛機離開邁阿密時寫的。每次坐飛機時,我都感覺那個進入黑暗包裹的過程猶如在子宮中漂浮。每次降落的時候,見到新的地方、新的感受從鼻孔、指尖、皮膚湧入,就像是出生在了一個新世界一樣。在飛行的黑暗裡,我想起自己有一次獨自在江浙一帶旅行,忘記自己怎麼走到一個建在城市裡的小坡上。坡野得很,黑得什麼都看不到。那裡本來應該有一個佛像雕刻在柱子上,但是太黑了,我什麼也看不見。於是我就站在那黑暗裡面,感受佛像好像就在我的對面。
筆名藿香樹,來自中國北京,在美國東海岸讀大學。

NEXT: 狐狸与月痴兽
麦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