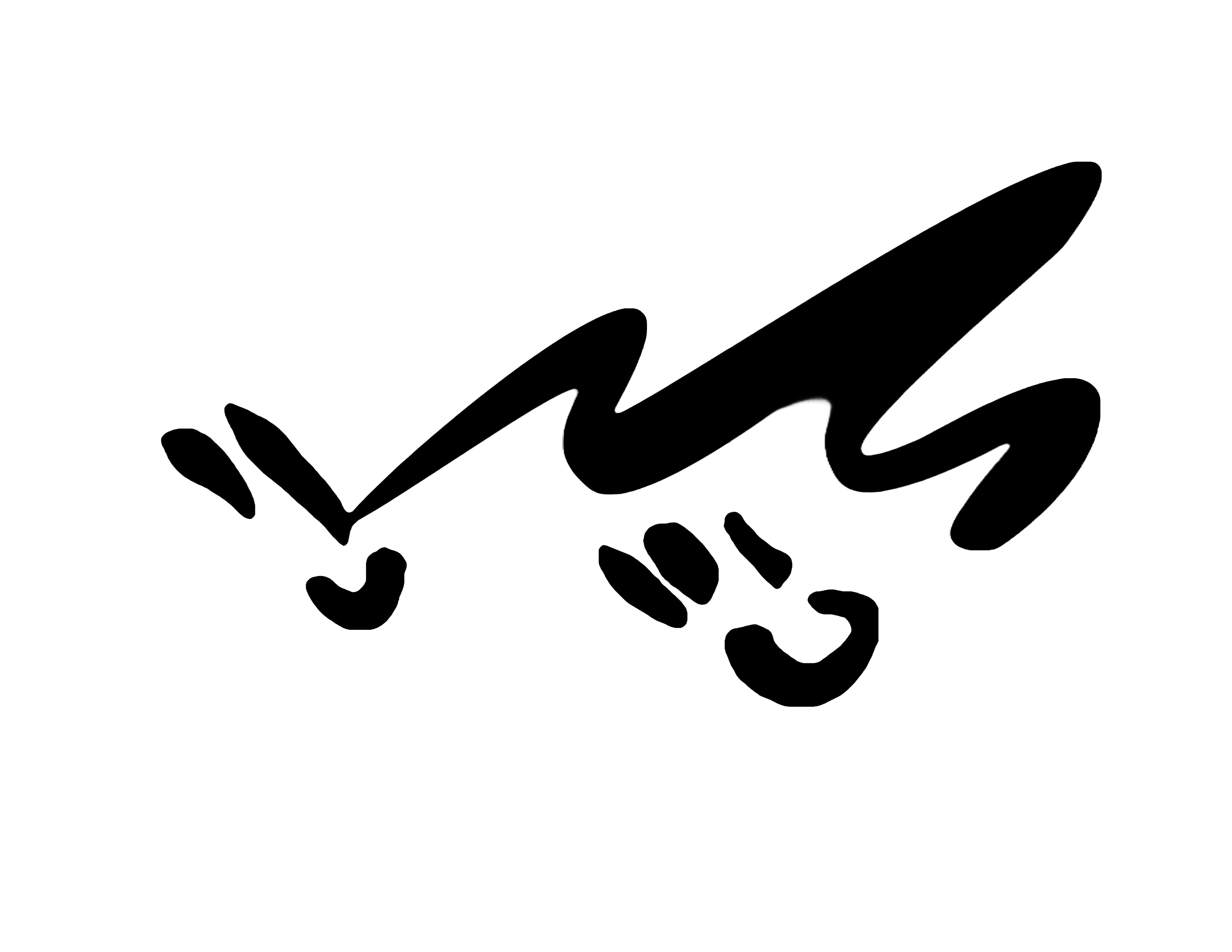火口鸵鸟
李凡

编者按:
我们每个人或许都经历过这样一个夏天。闷热难耐、万籁俱寂,好似被世界逼入死角。蓦地,你看见了那一只鸵鸟,它用它那坚韧不羁的眼神给了你再也无法忘怀的一瞥,从此在你心中生根发芽,永不消逝。
我失业的时候是一个夏天。老板说,欠你的钱再说。我知道他不会给我,因为实话说来,是我把他炒了。那一阵我要么躺在床上看电影,要么对着电脑打游戏,我打了很多游戏,从一个世界跳到另一个世界。炒掉老板的原因是钱太少,事太多。我说,我不伺候了。十三平的隔间还没到期,我把行李打了包,一堆纸箱子,能占掉房间的一半。我把它们放到公用客厅去,合租的人或许有意见,但我不在乎。
北京的天气很干燥,所以我要二十四小时开着加湿器,我家在海边,起床并不会嗓子疼。我给朋友打电话,我说,我的家伙什儿就留给你吧,这其中包括加湿器、洗衣机和一桌一椅,算是走之前给这个城市留下点痕迹,椅子座上还残存着我的头发和猫毛。猫已经死了,但毛还在。
正在我忙着发物流的时候,朋友来了电话。他说,你去不去看火山,听说能捡到他妈的翡翠。我说,捡你妈,石头都是一回事。但我还是答应了,因为他还听说那儿有很多姑娘。
我背一个书包就上了火车,朋友要求坐绿皮,慢慢爬过去,欣赏风景,我当然拒绝。他是个学画画的,立志要复兴国画,后来做了广告设计;我算是半个学文学的,立志要投身写作,后来做了广告策划,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
我说,要看风景,可以坐十一路,腿儿着去,他只好闭嘴。倒不是嫌累,因为他调了一天休,加上周末也只有三天假,就算能走到乌兰察布,也得留在当地放羊。他不像我,敢炒老板鱿鱼。
高铁很快,我们到了呼和浩特站又租了辆车。他执意要选八百块一天的霸道,而不要四百块的桑塔纳。于是我们开着霸道,路上的车越来越少,不到中午,我们就走在了一条没有防护栏,四周是平坦草地的柏油路上。我把头从天窗伸出去,草叶子味和牛粪味不住钻进鼻腔。我们确实应该租霸道。
这里的蒙古包和我想象的不一样,面积大过我隔间的三倍,砖墙和穹顶也很高,朋友的呼噜都变成了3D环绕。他开了一路车,确实该休息一会儿,但我不困,我失业的每天都在睡觉。
太阳毒得厉害,我一出门又钻了回去,取过朋友的墨镜戴上。我的头发很黑,把热量吸了个够,但我没有帽子,只好任由头顶发热。老板的院子很大,盖了十几个巨大的蒙古包,再旁边,就是一圈一圈饲养牲畜的区域,用铁丝网拦着。我溜达的时候又碰到了老板,他正在一个蒙古包下的阴影里剁羊排。他说,晚上整点吧。他说话的后鼻音很重。我们闲聊了一些,他说他有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很少回来,他这里也少有年轻人来住。我说,来看火山的不是都是年轻人吗。他说,他这里不能洗澡,姑娘们嫌脏。我瞬时觉得我们挑错了住处。他建议我傍晚再去看火山。我说好。我对火山本无兴趣,除非它真的可以喷出岩浆来,把我们都变成蚂蚁。
这群羊大概有七八十只,我站在栅栏旁观望着,因为它们总是走动,所以我数了几遍就作罢。我猜测它们没有出去过这圈栅栏,因为它们的指甲厚长,这是缺乏跋涉的标志,当然,让我下定论的还是那垛尼龙袋包装的饲料。生产力的进步让羊不需要到处奔波,只需在方圆三百米内,就可以吃喝无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好事。
一阵啸叫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穿过一个个蒙古包和一个大仓库,终于找到了它,一只鸵鸟。它也被拦在一片草地上,拦它的铁网比拦羊的网高得多,它也比我高得多,这个圈也小得多。它在铁网前来回踱步,步伐匀称,挺胸抬头,几乎无视我的存在。地上满是鸟粪,它粗壮的脚上也沾满了白与黑,混合成灰色。
我说,你在这嚷嚷什么?它没有回应我,继续来回踱步。它的眼睛很大,嘴里喘着粗气。我觉察到它的不对劲。它的左腿有些跛。我蹲下去,想观察仔细些。
“狗咬的。”老板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后,手里端着一盆碎骨。这时我才发现,在我身旁不远处的铁笼里,有一只熟睡的德牧,闻到肉味,它便坐起身来,嘴里淌着口水。我说,它比我都高,狗敢咬它?老板把那盆子扔进狗笼,“好吃好喝伺候着,让它咬谁就咬谁。”他笑得很淳朴。为什么要让它咬它?我问道。老板走过来,用脚踢了踢一根固定铁网的木桩,“松了,跑出去了。”我看着它腿上的伤口,半凝固的血水混合着黄色脓液。怎么不给它上点药?我说。“治好了又想跑了。”他回答道。我不再说话,他依然笑得淳朴。
闷热的下午漫长,由于实在没事做,我也仰到了土炕上,一直躺到外面变成深橙色。走吧,我说。朋友用鼾声回应,我便一巴掌扇在他脸上。看着他懵懂的双眼,我说,去看火山了。
这一路并不远,只开了五分钟就到了,我又开始觉得这车租得不值。山脚下停满了车,黄土与黑土的分界线,也是停车场和火山的边界。如朋友所言,刚走上了坡,便看到一群人蹲在一堆黑色的煤渣上拨弄着,只为寻找一种名为翡翠的石头。换个角度想想,他们又好似米勒笔下的拾穗者。姑娘确实很多,但都穿着宇航服,包裹严实,我没了兴致。
往上爬吧,朋友说。此时我们正站在最低的一座火口向下看着,眼前是一个巨大的碗,碗底满是煤渣。我转头,旁边有一座更高的,腰上盘着条狭窄的土路。我们费力爬了一个钟,终于到了更高的山口,方才眼里的大碗已经变成小碗。山上的风很大,我只穿了一件短袖,所以刚上来,就又想下去了。我努力想象着火口里的煤渣燃烧起来的模样,想象着挤满红油的沸腾火锅,从而让自己暖和起来。
如果真的能喷出来该多好?将蕴藏在地下的熔岩全部像爆米花那样迸射出来,无数生命随它一同消逝,草的、花的、蚂蚱的、蚯蚓的、蝴蝶的、蛇的、蚂蚁的、老鼠的、蜜蜂的,还有人的。我这样想着,浑身燥热,脚下的土地开始震颤。
朋友支起了画板,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没有很生疏,不一会儿功夫,一座火山就像模像样地浮现在纸面上,外面是绿色和土黄,里面是黑灰,天是橙蓝。他又像模像样地在一角写下“火山·印象”,惹得我一阵反胃。我说,你这山太死了。他说,你懂个屁。经过我的不懈坚持,他终于肯把笔交到我手上,我说服他的理由是,没有姑娘爬到这么高看他画画,他巡视一周泄了气。我挤了一大坨红色的颜料,一定要让他的火山喷发,让万物湮灭。我看着自己改编的作品,心底不由赞叹赫拉克利特的聪慧,火是万物之源,我愿意相信。
这里除了火山,再没什么新鲜的东西,当然火山也不怎么新鲜。我们能做的只是啃啃羊排,开车兜兜风,以及跟路边的牛马打个招呼。朋友画了很多“印象”,但每次都没有姑娘围观。我心里想着的也慢慢不再是姑娘。我时常要去看那只鸵鸟,也试过喊上朋友一起,但他觉得鸵鸟太臭,看一眼便又去画他的羊群。新来的老年团里,有两个大爷在看他画画,他不想失去这来之不易的观众。
它腿上的伤愈发严重,不仅没有结痂,反而附近都变得紫黑,脓水一直流到脚尖。我开车去到镇上买了喷雾消炎药,但每次我伸手进铁网,它都不再靠近我,或是站在原地眺望,或是在我和圈的边界间踱步。它的步伐越来越和矫健不沾边,但它没有停下,这让我费解。我不相信它是在为下一次越狱做准备,尽管它的视线始终在望向我这边,属于监狱外的一边。它或许是在用运动抵抗细菌,但是这却让伤口发炎更厉害了。我想了很多,直到我第一次看到它蹲下去。
我找到正在剁羊排的老板。我说,你的鸵鸟不太对劲,咱俩一起给它上药吧。我举着手里的喷雾药瓶。老板手里的砍刀明晃晃,满是油渍。“不麻烦,”他笑着说,“他们点了要吃,一会儿就宰了。”我看着正在凉亭里侃大山的老年团,一时有些语塞。老板是个亲切的人,每天的饭钱都给我们少算一些。
那只鸵鸟蹲在那里不再走动,仿佛得知了自己的命运。我第一次蹲下来与它隔网对视,它的眼睛很大,还长着美艳的睫毛。我忽然想进去看看它,这股冲动犹如画布上的火山。于是我翻越了那座栅栏,进到里面去,踩着泥土和粪便。我生怕惊扰到它,因为它如果突然发疯,我是招架不住的。但好在它始终安静地蹲在那。
我近距离注视着它的眼睛,它的胸脯像一个鼓风机,张开的嘴里不断吐出热气。
至少你出去过,我说。
我从圈里出来回到蒙古包时,朋友已经和老年团打成一片,他们在朋友身后围成一圈,一边传阅他的那些“印象”,一边看他临摹一头吃草的牛,画纸上没有牛绳。走吧,我说。朋友疑惑。我强行将他拽回了蒙古包。他问我去哪,我说收拾东西回家,他更加疑惑。我们是晚上的车,现在还不到中午。我说,别问了,走吧。他闷闷不乐,说大爷大妈晚上要请我们吃鸵鸟肉。我说,吃你妈,然后我就把他的东西一股脑塞进包里,拽着他上了车。我知道他不舍自己来之不易的欣赏者,尽管他们不是姑娘,但画画的人总是需要观众。
我倒车的时候,老板提着刀出来,眯眼笑着。这就走了,他问。他要上班,我说。老板挥挥手,老板娘执意要将一袋土豆装进我们后备箱,她说这是紫皮的,不一样。老板用钳子拧开了铁丝网的一口,把一根绳子系在鸵鸟脖子上。它跟着老板的步伐,缓缓向圈外挪动,有些吃力。老年团又围观上去。我踩下油门,反光镜里的鸵鸟、老板、沾满油的刀和老年团成员停在景深。院子的气压比外面高一些,驶出院门,我一下觉得眼前干净了。一路沿着平坦的柏油路开着,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几座火山依旧死在那。我在路边停下车,透过窗口望着它们,弯腰捡石头的人还在,比剪刀手的宇航员也还在,他们都和蚂蚱一样大。我想着,开下马路,穿过黄土铺成的停车场,飞向火口,一定是壮观的景象,如果能俯视脚下喷涌的岩浆,会更壮观。我给火山爆发找到了更确切的形容,它应该像被砍掉脑袋的鸵鸟脖子,血液一股脑飞出来。我印象里有过那种画面,鸡的脑袋被剁掉了,身体依旧挺拔,昂首阔步,甚至可以飞上房檐,这确实有些魔幻,关于记忆的真实性我无力考证。我发动汽车,不再去想这些事。我吃了那么多羊排,并没有对羊儿心生怜悯。它不过是一只被养来吃肉的鸵鸟。
离开火山不到一会儿,身后传来喇叭声,我从后视镜看到了一辆熟悉的车,是老板的那辆凯迪拉克。
他喘着大气下了车,脸上还有汗珠。
“看到鸵鸟没?”他笑着问道。
“什么?”我说。
“那个畜生跑掉了,”我注意到他手上还有血渍,他把手往衣服上蹭蹭,“刚抹了一刀脖子,站起来就窜,把客人都吓坏了。”
“没看到。”我摇摇头。
他踮着脚四处观望着,这附近连牛羊都没有。
“这牲口,你们慢些走。”他脸上又挂上了淳朴的笑,随后摆摆手,又上了车,原路返回去。
“你笑什么?”朋友疑惑盯着我。
“没事。”我点了火。
我期盼着能在路上碰到它,尽管我开得很慢,愿望还是落空了。我为它设想了无数种结局,最喜欢的一种,就是它脖子上留着血,腿上留着脓,昂扬着身姿,从柏油路奔到黄土,又顺着坡飞向火口。最差的一种,是它被德牧撕咬着腿,脖上套着绳子,拽回去砍头,宣示它第二次越狱的失败。
它或许会死,又或许如山底的顽石,永不消逝。

NEXT: 原丘
blurry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