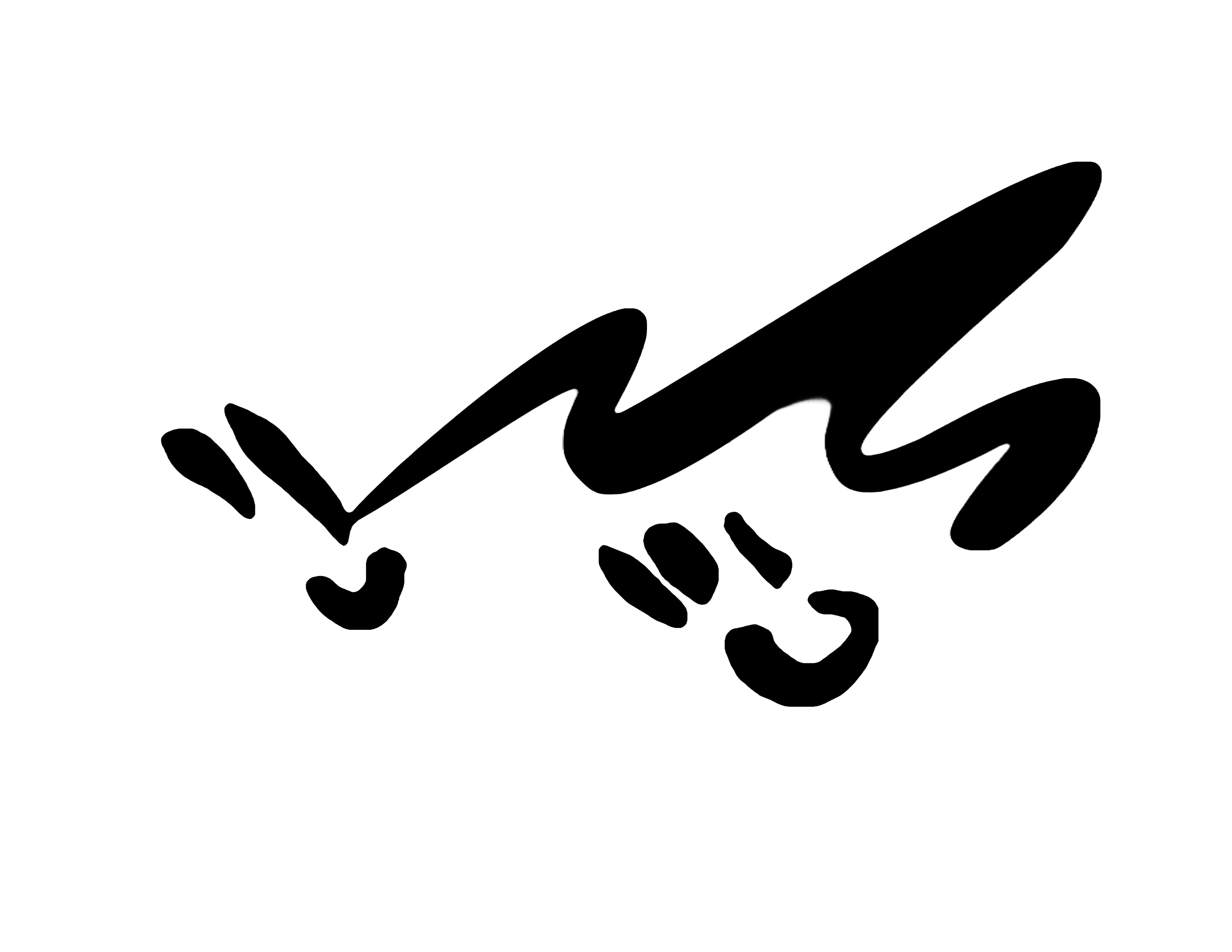曼哈顿岛所有土地已售空
略一

编者按:
给事物命名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居住在一个地方,度过一段时间,猛然拥有了一些记忆,于是就算是和它产生关系了,能够讲出一些故事,描述一些画面,乃至改变与被改变。作者对自己纽约市区中的生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有点像互相驯化——是了解、发掘,然后能够自信地讲出“真实”二字。即便这片土地早已“售空”,并不能够属于自己,人也仍然可以亲手开辟、锻造属于自己的经历。
“再见,我要去坐express了。”我跳下1号线红线,和朋友们挥手道别。
刚来纽约时,我经常搞错地铁的方向,是往南还是往北、uptown还是downtown。皇后区、布鲁克林这些名字从电影或小说里遥远的地名摇身一变,成了我生活的城市的一部分。
不得不承认,这里应当是世界上最不容易迷路的地方之一,东西南北道路地点,全部以数字命名。如真按苏格拉底说,语言之形式并非任意偶然,事物的名字反映了其所指的本质,那么如何命名一物一景也应有对错之分。可这个规律在纽约毫不适用。42街5大道,和123街30号西,最丰富多彩的世界被收纳于最单一的坐标,同质化的标识方式,让人错以为这两个“名”的实指也应无多少区别。但也许几串形制相似的数字背后,前者指向破旧失修的战前老楼,后者引人走到一整排摩肩接踵的大厦。一列列数字模糊了地名间的差异。人们想象中的纽约只有一种,那是曼哈顿中心的蓝色玻璃幕墙——谁又知道高楼未必都是蓝色,仅仅染着天的色彩,蓝天既是幕布又是倒影:有时我路过59街Columbus Circle,楼宇宽阔,高楼摩肩接踵,街道一侧是高楼,对面仍是楼,除去蓝天,日空澄净、阳光恰到好处时,对面楼的影子能映在此岸的高楼中央,仿佛走入镜中世界。

哈德逊河边的夕阳,映在玻璃上像油画
我总觉得,纽约是碎玻璃之城。不仅因为高楼宛如光洁的镜面,也因为纽约各处之间太南辕北辙,像一副颜色各异的拼贴画。唯有地铁不知疲倦地穿行其间,将毫不相干的地名相粘连。跳上一班地铁,仿佛穿梭时空,一时置身熙熙攘攘的市中心,来自世界各处的游客戴着“I Love NY”的鸭舌帽,举着手机自拍杆;一时又来到布鲁克林,走过的人衣着大胆怪异、潮流嬉皮。地铁最神奇的地方并不是为两个地点创造了空间上的连接,而是不容置喙地提醒着人们,这两处个性截然不同的地点同属这一片大地,甚至只要你跳进地铁,搭20分钟来回车,感受不到地铁左摇右拐调整方向,就来到另一个空间了。城市进化的速度如此之快,我们是落后于城市的动物,身在其中,神经感官还不能适应这样的跳跃。走出纽约的地铁站,时常有一种自己是某种冬眠的小动物,穴居已久、重见天日的错觉。
也许每一条地铁线路都有自己的灵魂。每次去法拉盛,坐上7号车,我最爱的便是地铁爬升,从地下回到地表,再转弯爬上高架线的时刻。落日时分,夕阳给远处高楼镀上金色的光泽,一侧是皇后区的标志性graffiti涂鸦建筑,眺望另一侧仍能看见曼哈顿高高在上的摩天大厦。7号线总有不少住皇后区的少数族裔,而周末去布鲁克林逛街坐上L线时,周围几乎是打扮入时的年轻男女。

架在楼之间的7号线地铁,高架上印着一些涂鸦
每个人也有一条最能代表自己之纽约的地铁线。我居住在上西区快三年,和所有在这里上学、定居的人一样,1号线的路线已烂熟于心。从搞不清方向,到现在,已能熟练地估算出地铁开到时代广场要停几站、要在哪里转车,比2、3号express快车线慢多少时间。
地铁载我至116街哥伦比亚大学站下车,我来到我的小世界。
往返于上西区120街校园附近与100街公寓的我,在即将搬离此处时,才忽然发觉这短短20条街道才是我的纽约。圣约翰大教堂、教堂边的医院和身穿蓝色制服的医护工作人员、一落地纽约便挨了两针疫苗的药店、每逢晴好天气便大排长龙的bagel店、最常去的可颂面包房……
这是属于我的真实。
若要踏遍这片街区,怎样走都可以。三年里,我骑过共享小蓝车,坐过地铁,也搭过巴士。有时迟疑要搭校车还是走路,刚迈出了几步便见着另一侧来了等待许久的大巴;有时慢慢悠悠过马路时,一侧信号灯已经转绿了,车流汹涌,另一侧的公交车还卡在马路中央,蓝色车身宛如搁浅的鲸鱼,身前是人潮穿行,身后是车的海浪。
偶尔赶时间,或是遇上大雨天,也会坐上一辆的士。可以脚步悠悠、可以大步流星;可以观路上行人百态,也可以戴着耳机在自我的世界内浮游。
不知多少次走过这短短1英里距离。这里不是曼哈顿中城,没有下城西村和东村密集的美食,没有大厦的天际线。曾和朋友们屡屡调笑这里是偏僻之地、远离世界中心。可这20来条街踏遍,编织出一处处独特记忆,才发现:这或许是人们称之为“家”的东西吧,我未觉察已拥有。
我曾以为,纽约排斥“家”的概念。这里的房子小逼仄、价格高昂。这城市的人行色匆匆、高傲又冷漠。这城市被寄予多少愿望,目送太多人来来去去。所以,我一向不愿在此托付太多期待——纽约是通往理想生活的中转站,是梦想的承托之地,唯独不会是家。它没有家的气息:不论去哪里,都躲不过臭水沟、垃圾和腐臭食物的味道;它也没有家的形状:纽约人不是在搬家便是在搬家的路上,刚把住处装点成喜欢的样子便要狠心丢弃所有成果、选出必要的物件,打点好轻简行装。它更没有家的模样:总是身一人、形单影只,许多友谊终结于一方离开这城市的时刻。
然而或许,这是“家”存在于此的形式。邂逅家的时刻,是咬下一口酥软可颂的时刻,是步履不停、穿行于繁杂街区、冲迎面走来的小狗微笑的时刻,是排队买bagel时听后面一群年轻女孩叽叽喳喳的时刻,是和伙伴结伴出游、去草坪晒日光的时刻,也是收到拒信,旁若无人地在公园长椅大哭、却被行人递上纸巾的时刻。
是在一个秋日夜晚,我犹豫了许久,终于第一次尝试共享小蓝车的时刻——晚风拂面时,心中难以自抑地涌出《城市》的旋律,我与五年前骑车上早自习、和着激昂的副歌用力蹬车、穿过早高峰人潮的我听着同一首歌。
路边的盏盏街灯、夜空悬着的月亮,几处光源映射出三五重影子,有的在我身前有的在我身后,追赶我也为我指引方向。我想起多年前时坐在妈妈电瓶车的后座,是同一轮明亮的月挂在天上,不紧不慢随着我们走。
月亮只是看着我。我问妈妈也问自己:月亮也会动吗?
抓得住的是同一朵云,抓不住的是曾经的梦。告别了故乡,纽约以一种另类的方式迎接我。即便大众所想象所熟知的那部分纽约一夜间折叠为白纸,我仍能在这片窄小土地自得其乐。夏日来临之际,我搬离居住了三年的上西区。如同夏眠的蝉褪去它的壳,栖居树木丛生的林荫深处,得以沉眠不问心事,呼吸一起一落间,才发现一部分自我已悄无声息剥落。
——
曼哈顿岛上所有的土地已售空。无法再开采,无法有创造。只有不断推翻不断重造,宛如来这城市的人,不断经历毁灭,不断有新生。
无法拥有更多土地,所能拥有的无非傍晚时的天际线与夕阳。我似乎在纽约找到了自己的月亮。
作者简介
笔名略一,现居纽约,从事数据/编程工作。喜爱文学,长期在纽约组织着一个线下读书会。希望通过文字捕捉到生活中的幽微与复杂。
创作意图
本篇作品是对纽约生活各种奇特之处的漫谈,也是在这座让人又爱又恨的城市生活快三年、数次搬家、最近刚搬离开自己最熟悉的街区的一次告别。

NEXT: 多语言者的困境
文学系在逃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