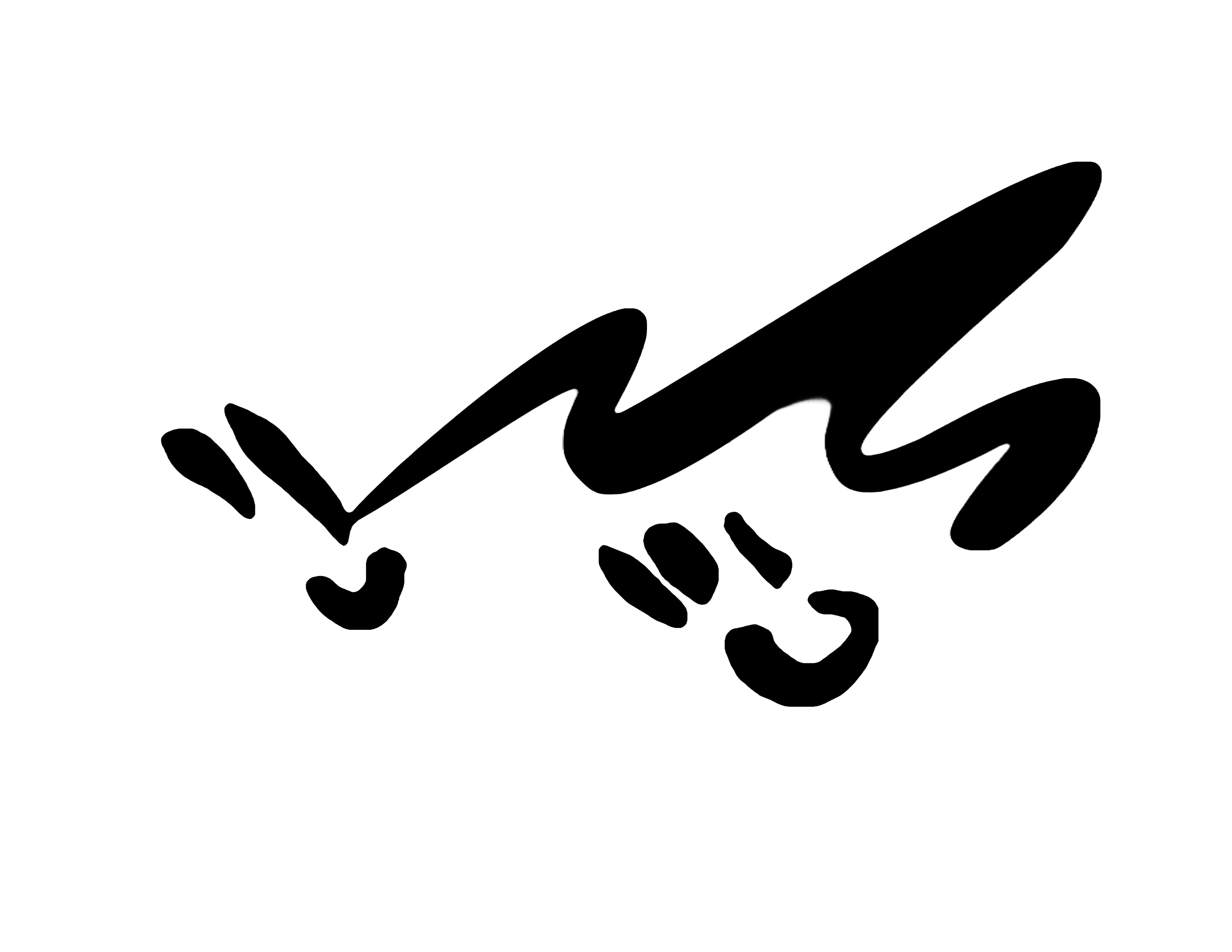异乡人
飞越边界_YUuKi

编者按:
多么有趣而可爱设定!通过小说的主人公艾鲁涅的视角,读者被迫从零开始练习“存在”。作者假借虚构的自白杜撰一个思维实验:假如我们把对身体——这最为物理性的存在——相关的一切假设抽离,会发生什么?我们共识或假设为真的,那些文化、常识、习惯、语言与名字,真的足够真实吗?又或者,二元地理解“物理”和“精神”真的足够我们触摸到“存在”本身吗?另外,所谓的“异乡”怎样地与现实生活中“漂流者”的身份重叠?(身在异国他乡,我们是否都可以指认自己为艾鲁涅?又或者,身边的人在我们的故地同样是艾鲁涅?)一遍一遍咀嚼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就像艾鲁涅一样——穿越一条幽暗隧道,落进一副躯体,诞生到这个世界上。
艾鲁涅恨她的身体。
这不是因为她的身体得了场大病,让她的生命力再也不如从前。这也不是因为她正在得病,她有什么病呢?她很健康。也不是因为她想要自杀,她有什么理由自杀?她的生活一帆风顺,她没什么可抱怨的。艾鲁涅对她的身体没什么意见,她的身体有富有美感的曲线,因附着于骨头而怎么揉也揉不变形的肌肉,她有十根手指和十根脚趾,两只手和两只脚,一个脖子一个头,有感受不到触觉的头发。
她不算很胖也不算很瘦——谁来定义胖瘦呢?她不算很高也不算很矮,刚好够她能和别人眼睛对上眼睛,不需要低着头也不需要仰着头。当然,她需要仰头看向天空,看看天上有没有云,太阳是否落山;或者低头看向大地,她需要蹲下来或躺下来,才能看到草的纹路和蚂蚁的行径。她能听到她应该听到的声音,她的耳朵没有问题。她能走到她想要走到的地方,她的脚没有问题。她可以说话,尽管她不喜欢学很多高深的词汇,只需要让别人知道她在想什么,她想要什么,就足够了。她的眼睛被形容为“像被装在湖泊里的星空”,其实就是一双黑色的眼睛而已,她也没瞎。
她的身体已经值得被很多不如她的人羡慕。但是,依然,她讨厌她的身体。她会专注于跋涉途中浸湿她衣服的汗水,这不仅让她又臭又湿,还让她在没达到预期地点的时候就疲惫不堪,拖累她为自己设想的进度。她的皮肤会觉得很痒,她需要去挠,为什么人要挠痒痒?她又不想让自己痒,是皮肤想这么干的,皮肤里面有那些细胞,还有什么神经——真吓人!她自己里面装了这么多她看不见的东西!艾鲁涅讨厌去看医生,因为她听不懂医生们说的话。她当然听得懂他们说——艾鲁涅小姐,您的膝关节有轻微磨损,您的皮肤有一些过敏——她当然知道自己的身体有这个毛病那个毛病,因为她每天都在用它!不用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就像从来没被翻开所以一直很新的书,或者从来没被人开垦过的树林。
于是戴着眼镜的医生——他一定眼睛有毛病才戴这个玩意——告诉她要每天注意休息,少去草丛茂密的地方。但是这样根本说不通,艾鲁涅需要走路才能去到附近的集市,她需要走路才能认识她需要认识的人,她甚至需要走路才能来到这家诊所,而现在他们要求她不要随意走动,这当然就不会让她的“膝盖”继续“磨损”了。艾鲁涅喜欢到草坪去晒太阳,所以那个建议行不懂,她不会为了自己的皮肤而不去草坪晒太阳的。
医生建议给她开另外一些药方,嘱咐她每天给膝盖涂抹一点这种药,每天再给皮肤涂点那种药。艾鲁涅不喜欢每天给自己发配任务,她的任务已经够多了,都是别人给她发配的。医生就给她开了另外两种药物,当她膝盖疼的时候涂一点,当她胳膊或者腿或者背部痒痒的时候涂一点。“这是必须做的,艾鲁涅小姐,”他这样说,“我需要对我的病人负责。”
于是艾鲁涅交给他应该交付的钱,拿着一包药草粉末和一罐药膏走了。
她需要涂药吗?她需要。她希望她不需要,但是这些身体上的小毛病真的很麻烦,不过是在哪些事情上浪费时间的问题罢了,她知道如果她在保养身体这方面多花点时间,她就能少花点时间去为自己的身体发愁,然后有更多的时间去……完成别人分配给她的工作。
她真的讨厌工作。她讨厌需要花钱才能得到东西的自己。她本来不讨厌钱的,现在她讨厌了,别人的钱自己的钱都一样。艾鲁涅在一座叫做蒂瓦纳的城镇工作,这个城镇整天都有运不完的矿,它们来自城镇旁边的山脉。那座山脉叫做莉兹贝特山脉,艾鲁涅的工作地点叫做鹿头小馆。真够愚蠢的名字。艾鲁涅不喜欢每样东西都有名字的世界,如果她不跟别人说某样东西的名字,他们就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甚至于她如果不告诉别人她的名字,别人就根本不把她当回事。每个人第一句一定是问她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名字!名字!
如此可见,艾鲁涅差不多讨厌任何东西,她认为这个没必要,那个也没必要。不过,她大概是没有真正讨厌她自己,或者说,她不讨厌她定义的那个“自己”,她喜欢艾鲁涅,尽管她不喜欢艾鲁涅这个名字。但是她总要习惯的,艾鲁涅只需要完成必要的工作,等机会来了,就可以不再忍受这种非常奇怪的生活了。
别人一定看不出她的想法。别人眼中的艾鲁涅,是个充满活力,通情达理的年轻女孩,和她的大部分同胞们不一样。艾鲁涅并不是想这样表现自己的,艾鲁涅只想快点回家,她不属于这里的生活,她也不属于她的身体。
艾鲁涅是世外之人。
这样说可能不准确,她的确来自一个世界,只是不是这个世界。实际上,这个世界有两个世界,是大世界包含两个小世界的关系,或者以某些学者的措辞来讲,是集合和子集的关系(艾鲁涅不懂数学)。两个小世界之间其实是被隔离的,两个世界的居民其实本来不认识对方,艾鲁涅其实本来不属于这里。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现在的确在这里。大家知道她是怎么来的,有很多和她一样的世外居民——异界居民——不小心来到了这里,通俗一点讲,就是顺着世界之间的空隙“掉”进来了。艾鲁涅从原本的世界掉到这里,她的生命也随之掉进名为身躯的容器。因为你看,她原本所在的那个世界,是不需要身体这种东西的。
这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本来“另外一个世界”存在这一事实,也绝不算能够很快被人接受的事情。许多小孩子没长几岁,然后他们也不信这茬儿,他们宁可相信海里存在大海怪,云端存在天空之城。但是让他们相信这一切之外另有洞天?不可能,绝不可能!
我们没有办法看见那个世界长什么样子。的确,如果我们看见了的话,我们就不至于不相信它的存在了。它的确是存在的,只是人们看不见它,这不是因为有什么东西遮住了它。不论一个人如何死盯着大海的彼岸,或者天空的边界,都不可能看见艾鲁涅原本所在的世界。至于这是为什么,没有人知道,艾鲁涅也不知道。艾鲁涅本来也不相信她的世界之外别有洞天,但是,她现在在这里了,眼睛是不会说谎的。
你可以理解为这两个世界互相重叠,或者处于不同的时空位置,或者被看不见的屏障隔离。总之,人们看见了艾鲁涅,也看见了很多和艾鲁涅差不多境遇的“人”,他们虽然长得和人一样,但内核还是来自异界的生物,因为他们诞生在别的地方。他们是不一样的。
艾鲁涅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她在意识的海洋里——你可以这样形容“那个世界”的生命交流形式——游泳。突然她被卷入某种看不见的漩涡,她的意识想往上走,却正在往下走。这对她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事,她怎么能够想但是没做到呢?她努力去想在她之上的地方,但她继续坠落、坠落,直至达到高度的最底端,摔在属于这个世界的某个街道上。
艾鲁涅不觉得新世界有好好欢迎她。实际上,当时聚集在她周围的人群之多,让她以为被某个强大的意识体抓住了把柄,被丢入了某种可怕的幻象。她试图感受那假想的敌人在思考什么,她对自己攻破意识防线的能力很有信心,但不论她如何延展她的意识,都发现它无法逃离这个小小的界限。艾鲁涅发现她好像真的不是她自己了,他们解救了她,给她穿上衣服,给她吃东西。他们登记了她的身份,告诉她没什么可担心的,像她一样的异界来客比比皆是,她只需在这里找到想做的事情,等他们想办法把她送回原本的那个世界。他们写下她的性别——艾鲁涅当时还不会说话,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只是觉得他们在做与她相关的事情——然后问她希望他们如何称呼她。
艾鲁涅哑口无言。他们又仿佛早就预料到她的反应,请来一个和他们长得一样的生物,那个生物嘴巴紧闭着,让艾鲁涅听到脑中响起了声音。那个和他们一样的生物说,我和你都是那个世界的原生居民,并向艾鲁涅转译那些人在说的话。
艾鲁涅盯着他看。非常诡异的形状,很高,有恶心的枝条,还有恶心的长毛,两个像蛆虫一样圆溜溜的,会转的小东西,像蛆虫一样的会动的红色东西。她花了好久才被说服,开始相信他的确是自己的同胞,因为他说明了关于“那个世界”的种种事情,譬如大家讲话绝不像人类(艾鲁涅当时不知道人类是什么)一样慢,也绝对没有外形这种麻烦的东西。艾鲁涅完全同意,她发现自己可以和他顺利地交流,心里的沉痛少了很多。之后,他问她,你希望我们如何称呼你,意思是你希望其他人提到你的时候,应该用什么词提到你。
艾鲁涅觉得不可思议。就像她记住了他的意识特征一样,他也无需其他说明,就能够在茫茫人海中识别出她的身份,除此之外还需要什么?他说在这里就需要换一种识别方式,因为人类是无法不开口就能讲话的。他告诉艾鲁涅不必慌张,试着用嘴巴发几个音,看看能讲出什么来。他说他当初就是通过这种方法,确定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名字”。
艾鲁涅不知道该怎么做。她挤压自己的喉咙,舌头蠕动着和牙齿摩擦,她的声带在颤抖,口水把嘴里搅得一团糟。她可以发出声音,她可以听见自己的尖锐的嗓音,但是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她永远也不会理解这些东西的意义。
那些人擅自替她决定了。他们认为她的发音与“艾鲁涅”相似,于是就写下了这样的名字。其实她的确说出了类似“艾鲁涅”的声音,但肯定还是和它有区别,那些人并不是很在意这种区别。艾鲁涅觉得既然他们没有意见,那她最好也不要有意见,她最初在这里体会到的规则,就是要依照这个世界的规则行事,以他们的逻辑去思考问题。
他们把她安排在楼里的某个房间,让她好好地睡一觉。她花了好久才明白,睡觉的意思是闭上眼睛,然后变得什么都不知道。
“晚安,艾鲁涅。祝你做个好梦,或者什么梦也不做。”
她在纳闷那些人在跟谁说话。然后,她发觉那个发音很熟悉,木讷地朝他们点头。为什么她要点头?她觉得这时候就应该这样。
艾鲁涅不敢睡觉,但是她实在太累了,眼睛酸痛,心脏也砰砰直跳。她觉得睡觉真的太可怕了,因为睡觉的感觉就像是死了一样,还好第二天早上她成功醒来了。
艾鲁涅经常思考为什么。她不经常问,她经常想。
但空想是不能为她带去答案的。所以,她只能去学习语言。
她不明白单纯的声响到底有何用处,除了让世界变得嘈杂。她会在原野上躺下来,偶尔听见甲虫和飞鸟的声音,河流和雨滴的声音,马车和火车的声音。它们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没有意义却依然存在。没有人去思考虫子的翅膀为什么和鸟的翅膀摩擦的声音不一样。狼群的嚎叫与士兵的战吼有何不同?日月和星辰为何沉默始终。钟表的指针告诉大家时间在流动,然而时间本身并不会说话,甚至不能用任何证据去证明它的存在,除了人们口口相传的“时间”这个词语。玻璃摔在地上迸裂出刺耳的声音;婴儿以哭嚎为媒介获得他们的新生,饿殍在无人知晓的荒原静静死去;火烤着鹿肉发出滋滋的响动;狗听见主人的摇铃开始垂涎欲滴,饭桌上的咀嚼声是最有效的消化药。
为什么面包叫“面包”而不是“包面”?为什么鸟叫“鸟”而不是什么,“飞狗”、“虫”,或者其他的名字?谁定义了它们最初的含义?后来,艾鲁涅从吟游诗人的口中得知,某位女神将字符洒落人间,看着人们将它们组成实意。语言学家告诉艾鲁涅,如今的一切语言都有共同的根系,由于种种原因而演变成现在的样子。街头小贩瞪了她一眼,说这个问题并不能帮他多挣几丁钱。
丁,米拉,赛克,摩奇洛——艾鲁涅花了好久才记住它们的名字,以及它们的统称“达尔他币”,以及这种物品的总称,“货币”。把金属做成小小的圆形,再刻上文字和图案,然后人们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铁片能买到小麦和鱼,铜片能买到糕点和熟食,银片能购得房屋,金片艾鲁涅从没有过。与此同时,从山脉里捡来几块铁矿铜矿,就不能换到比几杯水更多的东西了。
似乎什么都能被冠以价格,泥土也有价格,甚至空气也有价格,天空也可以有价格,只是没有人这样说罢了。被称为国家的区域有自己的价格,飞艇未经允许经过空域要被罚钱,没钱付房租就从屋子里滚出去。价格越高的东西,就越被人们喜欢,但是价格太高又被某些人记恨。比如,艾鲁涅穿着款式优美的鹿皮大衣在街上走着,得到了很多路人的赞美;她拎着朋友送她的一个小包,就被投以鄙夷的目光。后来她才知道,这个手提包的原价有数千摩奇洛,而朋友送她的是一个仿冒品。
“现在大家都用仿冒品,”朋友对她说,“但是别说出去,不然你会遭人嫌弃的。”
“仿冒品比真品高吗?”
“你说价格?不不,正因为是便宜货,大家才会去买呀。”
“所以它更便宜。”
“是的,它是仿冒品。”
艾鲁涅总感觉喉咙里憋得慌,但是她也不知道如何形容她的疑惑。总之,不论别人认为她拿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都会讨厌她。她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把那个手提包还给朋友了。
“哦不不,这是礼物,你得收下。”
“谢谢你,我现在不需要它了。”
“哦,不,不你务必留着它,这是我的一份心意。”
艾鲁涅只好把这个手提包放进抽屉,再也没有带着它出门了。人们的情绪是很轻易能察觉到的,不论他们如何沉默,或者如何用语言去包装他们的想法。像她一样来自异世界的生物,是很容易能察觉到这些东西的,人们管他们的能力叫做“精神交流”。艾鲁涅不觉得这种交流有什么奇怪的,对她来说,这就是正常的沟通手段,只是名叫人类的生物根本无法以这种方式交流。
社会的法律规定像艾鲁涅的人,不得通过精神交流去侵犯普通人的“隐私”。于是,艾鲁涅只好去学习语言,她需要知道怎样去和普通人说话。偶尔,她和同胞们会使用原始的方式交流,而在普通人面前,他们又要顾及到别人的感受,将自己想说的话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不然就是“不尊重别人”。
艾鲁涅其实挺受人欢迎的。她学会回应每个人的问候,回答每个人的问题,她是一个完美的柜台服务员该有的样子。她很聪明,一般人想不到的点子她都能想到,她经常被人夸赞。艾鲁涅不觉得一句“你好能干”或者“谢谢”很令人鼓舞,不过她隐约感应到的那些人的“精神意识”,在散发让她切实体会到的诚恳,这样艾鲁涅就能确信,他们是真的觉得她很好。不然的话,如果艾鲁涅只感受到冷漠的精神意识,她就明白,那些人是在欺骗她。
艾鲁涅不喜欢被骗的感觉。久而久之,她遵循同胞的建议,决定不去感应别人的精神了。如果她不感应,她就不会知道她是不是被欺骗,也就不会觉得伤心了。
不论工作如何繁复,艾鲁涅也从未将身体上的劳累,和心灵的平静相互联系。每天傍晚下班之前,她都对店铺进行最后一番打扫,这样她才认为一天的工作能正式收尾,尽管其他同事几乎是要把门撞碎般跑出去的。下班之后,艾鲁涅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的住所度过,照料自己的花草,看着街上的布景发呆。世界如此嘈杂,然而她的世界却如此寂静,她总会在百无聊赖的氛围的鞭策下,跑到外头去消磨时光。
现在的生活是暂时的。等到机会来了,她就能参与到某种仪式,顺着把她送到这里的“异界漏洞”,原封不动地返回她原来的世界。人们管这个仪式叫做“归零仪式”。零,从手写体的角度看,就是孔洞的形状。傍晚,艾鲁涅用手圈一个圆形,将夕阳圈在里面,想象着在夕阳的背后,她的家在等着她。
艾鲁涅说不上喜欢现在的生活。但她目前的境遇,的确让她少了很多很多,所谓的普通人的烦恼。
艾鲁涅会做梦。梦境的体验让她回想起在故乡的感觉,大家没有形体的隔阂,只有纯粹的意识与意识之间的交融。她梦见各种东西,很多时候,她已经忘记她都做过什么梦了,只记得那个梦令人愉快,或者令人烦闷。
有一个梦让她记得死死的,她不明白它为什么会是那样的,但那是个关于吸血鬼的梦。她没有见过吸血鬼的样子,实际上吸血鬼被认为是不存在的生物,不过像艾鲁涅一样的被称为“精灵”的生物,曾经也只是存在于童话书里的虚构产物,所以艾鲁涅对吸血鬼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不是特别有自己的看法。在这个世界,“事实”也不过是包裹在“言语”里的容物,很多猜想是无法被证伪的。
做那个梦之前的很多天,艾鲁涅都觉得心情不畅。她不明白自己到底怎么了,她能够清晰地思考,她能够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她的西尔维亚语学得还不错,至少是在日常用语方面——但是在她离开人群,与自己独处在小房间的时候,她总觉得内心很不舒服,有某种情绪在脑中不断放大,让她呼吸困难,最终嚎啕大哭一场,怀着恐惧和不安沉沉入睡。她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不对的事,她遵纪守法,她按时完成她的任务,她交了很多朋友……半夜她想要起床喝水,发觉自己的身体如此抗拒她的意愿,她不想动,她也不想思考任何东西,就像是她一下子花光了所有的力量,只剩下想要寻求安稳的本能。
这在她看来,是前所未有的怪事。人怎么能够想做却做不到呢?艾鲁涅向医生询问这件事,医生看起来不以为然。“你能够想一想就能飞吗?”他问她。不,艾鲁涅说,但在我的故乡可以。我们可以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只要我们的心灵足够强大。但是这里很奇怪,我能够看到云端的飞鸟,却无法像它们一样翱翔。
“那是重力在拉扯你,”医生指指脚下,“我虽不是物理专家,我也知道,再强大的意识,也无法逃离重力的束缚。”
“重力?没有了重力,一切就能飞了吗?”
“谁知道呢?我无法想象那种情形。”
“如果我有翅膀,我就能飞了吗?”
“你没有翅膀,艾鲁涅。你的身体太重了,你的大脑也很大。”
艾鲁涅站在高高的天台上,向下俯瞰街道。踩在空气上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总有些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谁会做那种蠢事呢?她从天台的边缘退下,再也没想过飞翔的事了。
在梦里,艾鲁涅怎么跑都不会觉得累。她可以说话,但她听不见声音。她喜欢这种感觉,这和在她故乡的感觉太像了,她会在入睡前祈祷能够做梦,如果她早上起来发现自己没做梦,或者不记得自己的梦,她会感到非常失望。如果没有工作的话,她就可以一直尝试入睡,一直去尝试做梦了。
在艾鲁涅的那个梦里,吸血鬼是稀松平常的事物。它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所以当艾鲁涅知道自己家里也有吸血鬼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么惊讶。毕竟这是个梦,就算吸血鬼真的能把她吃了,那也是在梦里把她吃掉而已。但是她也知道,如果在梦里面死掉的话,这个梦就会迎来它的结局,艾鲁涅不想很快地结束这场梦,她不是每天都能梦见吸血鬼在她家转悠的。
于是艾鲁涅开始逃离吸血鬼的追击。那个吸血鬼浑身漆黑,让她感到很不舒服,她讨厌黑暗,她的故乡本来就没有黑暗这种颜色。她知道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自己就会落入吸血鬼精心布局的陷阱,她居然开始期待起被吸血鬼抓住的那一瞬间。人的身体非常脆弱,艾鲁涅又很怕疼,但这是梦!在梦里,她可以体会到死亡的感觉,实际上却还活着。
艾鲁涅推开门,义无反顾地冲向看不见的陷阱。视线被一切两半,再切成好几块的时候,她感到异常兴奋,她的身体七零八碎地落到地上,因失去生命而变成被重力束缚的死物。同时艾鲁涅的意识越飞越高,俯瞰吸血鬼吞食她的肉体的画面。艾鲁涅还想多看一会儿,可惜梦境很快就结束了,她不得不陷入更加黑暗的沉眠,然后在阳光明媚的清晨醒来。
“这可真是个糟糕的梦……什么,你喜欢它?”
医生以一种看天外来物的眼神看着艾鲁涅。艾鲁涅觉得困惑了,她不能喜欢自己的梦吗?
“好吧,我觉得你应该去休息一下,可以给维克多先生请个假。这是我给你写的假条,你可以给他们看。”
艾鲁涅看了看假条上的字眼,从惊讶变成愤怒。
“为什么这是个病假条?我没有得病,我非常健康,难道喜欢做梦也是一种病吗?”
“嗯,艾鲁涅小姐,您也许没有察觉到。但您现在的状态,在我们的定义里,就是在生病。在病情恶化之前,我们希望您得到充分的疗养,这是我工作的意义所在。”
“我没有得任何病!”
艾鲁涅摔门离开了诊所。她真的很想把病假条扔进街边的垃圾桶,但是想了想她还是没有那样做。到底要不要请假呢?她认为自己没必要请假,所以她把这张病假条塞进抽屉,和那个手提包关在一起。
“是的,维克多先生。我觉得是时候了。”
“你要知道,这件事不是我能决定的,你应该给他们写一封信,问问这样办行不行。”
“维克多先生……您说时间一到就可以走的。”
“请不要表现得像我欺骗了你一样,”维克多停止了浇花的动作,站起来面对她,“你不能今天跟他们说要走,明天就能走成。你需要按照程序来,明白吗?按照程序。”
艾鲁涅总觉得这个说法非常奇怪。不过一想到在这里,任何事情想要做成都要消耗时间,她又觉得不奇怪了,只是感到心里不爽。空想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她需要提问。
“好的,那我该怎么做呢?”
“我跟你说了,你去给把你分到这儿来的人,写一封信,或者打一则通讯,或者见他,总之把你的诉求传递给他,然后他才能知道你的诉求。”
“好……吧。”
“这不困难。我有那个人的联系方式,你就这么做吧。”
迪安·阿兰·斯普拉斯。艾鲁涅读着拗口的名片,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琢磨。哦天,写一封信并不难吧,她早就知道怎么写信了,她也知道该如何措辞。但是这样做总是很怪——你看,她不知道那个人长什么样,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样的性格,她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他,一张纸就能说服她帮自己的忙?要如何用文字表达急迫的心情呢?总不能写一大度感叹号,外加一大堆语气词吧,那样的话也太不礼貌了,而且也不“正式”。如果他能理解她的处境就好了,人们需要付出什么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把自己的想法转化成书信也需要时间。
如果他觉得她不礼貌该怎么办?他完全可以看一眼这个东西,就把它丢进垃圾桶,把艾鲁涅这个名字忘得一干二净。艾鲁涅想直接冲过去找他说明这件事,但是说又要怎么说?如果他拒绝,那就完了,艾鲁涅要被永远困在这里了。她听说和“那个世界”连接的“通道”有开启的时间限制,她不懂具体的原理,总之如果再犹豫下去,她就要错过回家的时机,然后再等待天知道多长时间了。
她想了一会,还是决定先用纸笔整理她的思路。她需要逻辑和足够的情感表达,以及恰当的利益……那个词怎么说来着,修辞,对,修辞。
她试着回想自己当初来到这里的心情。那时候她没有选择,可是现在她却感到恐惧,她担心她会做错误的决定,将她带入无法回头的死胡同。如果她就此离去,她将不能再见到维克多先生,不能见到她的朋友们,不能见到她的衣服,她的鞋子,她的床,她的房间,窗户里的景色,街道上的景色。她将不能闻到每天早上问候她的咖啡香,不能尝到偶尔飘进嘴里的头发的味道,不能触摸滑腻的花朵的茎叶。通向这里的门将永远向她关闭,然后她甚至不能定期向这里的人寄信,这里的人也没办法给她寄照片过去,因为那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物质”这种概念。
一种陌生感让艾鲁涅脊背发凉。她不确定这种感觉是何时产生的,也许因为她太久没有想过故乡的事,就把它的感觉忘记了。她试图回想自己在那边的生活,自己在那边的朋友,又害怕等她回到他们身边的同时,她会失去他们。她害怕自己会被他们遗忘,也害怕她会被这个世界的人们遗忘。她又没有死掉,所以她也没有能记录自己的墓碑,只有随时可能会损坏的照片。
她考虑用相机给自己多拍几个照片,或者录一段影像,送给她在这边认识的人。但那又有什么用?物质终究会消失的,化作看不见的尘土,回归最原始的大地。而如果她不回去,那么终有一天,她也将变成尘埃,失去她最为珍惜的思考的能力。她为这个事实感到悲哀,她是如此弱小,她甚至不能控制自己的时间。而在她的故乡,她可以控制一切,只要她想。
她忽然意识到,意识也是有其边缘的。总有一些事情是在她的想象之外,她并不是万能的,她的世界也不是世界的全部。如果没有这次旅程,她不会知道自己还可以有一个名字,不知道她可以有一个好听的嗓音,不知道镜子里可以照出她的容貌,不知道事物可以有形状和颜色。艾鲁涅将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叫艾鲁涅,也将永远不知道她所不知道的事情。她将被困在名为常识的牢笼,让愚昧导致的自信将自己埋没,她将会在无知中走向自己的坟墓,坟墓之前没有人为她献花。她的故乡根本就没有花。
多么无聊的世界!艾鲁涅羞于对故乡产生这样的想法。
但是依然,她需要回去。人们从母亲的肚子里出来,艾鲁涅在这里并没有归属,她将永远是一个异乡人。旅程要迎来它的尾声,艾鲁涅这样说服自己,拿起异常沉重的钢笔。
尊敬的斯普拉斯先生……
作者介绍
被迫转理科的文科生,骨子里还是保留对写作的热爱。平时有在自己创作虚构小说,也有在创作现在流行的OC(original character)相关的故事,非常乐于讨论和分享写作感悟,希望以后也能在小说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创作意图
说实话,看见“容器”这个题目,我第一时间就想到“身体是精神的容器”这个主题。我希望通过从一个虚构外来种族的视角,去体现“身体”和“精神”之间的关系,它们如何能够相互影响,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冲突。当外在环境需要我们必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平衡内心的诉求与外界的要求。我觉得思考这个问题,在当今的社会显得愈发重要,如何适应繁复而快节奏的生活,同时给内心的净土留出一片空间,这件事说着容易,做起来难。
我不希望在我的故事中体现某种“说教”的倾向,我也没有想要仅仅通过一则故事,去给出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我本人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答案。但我确实想用我的故事,去带给读者一个相对容易接受的“体验感”,并且通过这种富有体验感的叙事,去传达一种我想让读者理解的,旨在反思我们自身的思维模式。通过设定一种“本来依靠纯粹的精神交流”的外来种族,将这个种族的意识放进人类的躯壳,我试图以这样的“非人”视角跳出我们的常识,去阐述到底是什么在容纳我们无限延伸的精神世界,并且用精神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冲突,来解释一些我们可能会遇到的,看似难以应对的精神困惑。身体是容纳精神与思想的容器,社会是容纳个体的容器,社会规训是本能和欲望的容器……我常常以这种包含关系去思考自身所处的境地,然后就明白人虽沧海一粟,但依然有值得去期待,去奋斗的事物,这样一种说出来简单而悟出来难的道理。
关于标题的“异乡人”,其暗含的意思,一个是点明艾鲁涅来自异乡的身份——不论她如何被异化为这个世界的存在,她的归属终究不是这里——另一方面,也暗含异乡人总归是有一个能够回去的“乡”的。至于这个“乡”具体是什么,我认为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它可以是地理意义的,也可以是精神意义的。我认为人从一个地方来,到一个地方去,心灵总还是要寻得一个有归属感的地方。对于主人公艾鲁涅来说,她的精神内核远离她的故乡,而也许她在故事之外的某一时刻,也会意识到,物理意义的隔离,也许并不会阻碍她的精神“归乡”。

NEXT: 雪
王嘉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