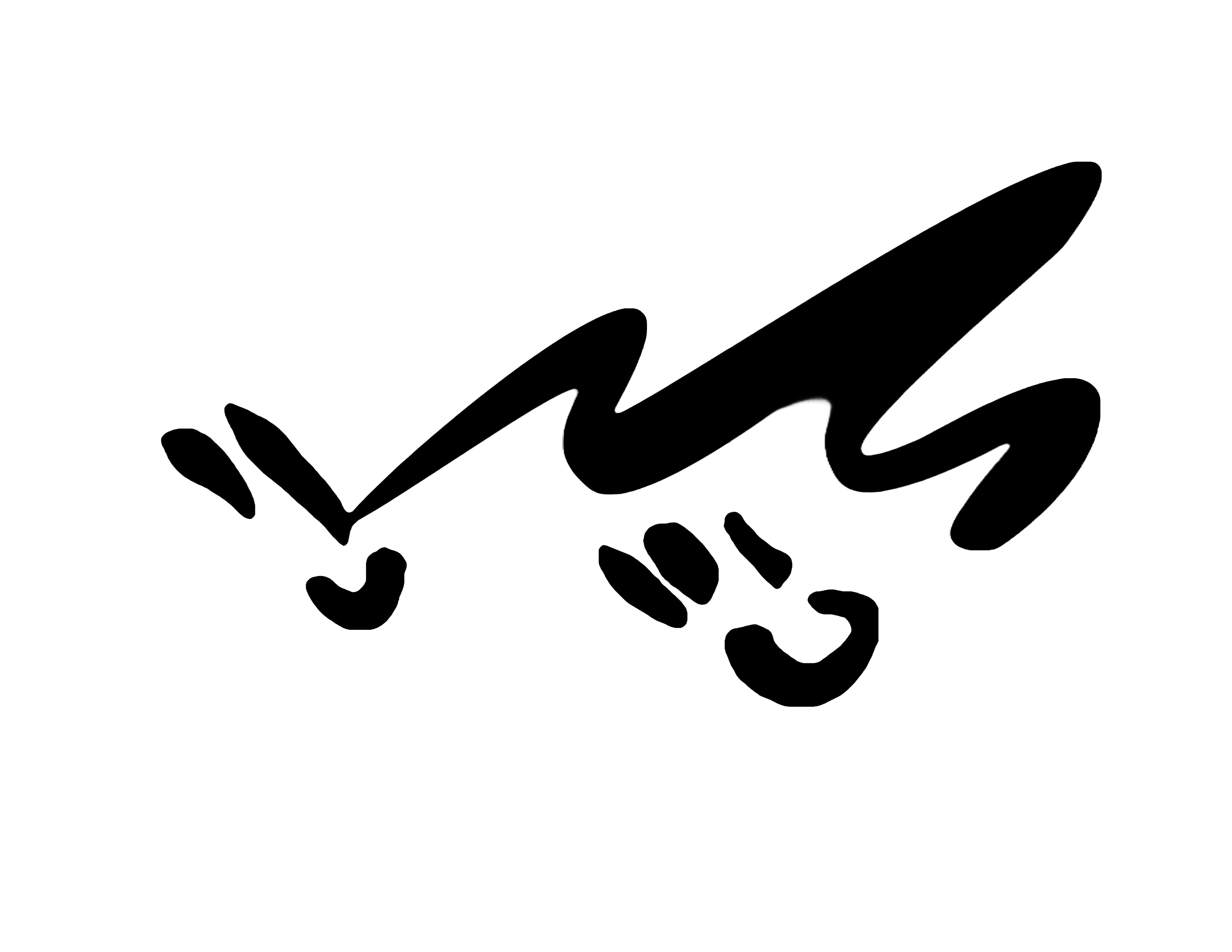多语言者的困境
文学系在逃饿女

编者按:
“多语言者的困境”一节中,我们了解到,一方面,能有机会有能力习得并熟练使用许多种语言是多么令人羡慕的特权,然而另一方面,语言并非真相——词语背后并非一比一地挂着实实在在的真理。正相反,语言的板块之间时常有裂隙,引诱我们走向一种骗术,看起来深奥,实则空无一物。作者真诚地将语言摆放,表达这种“平静的恨”。
“在法国读文学”一节中,我们看到和语言相关的学科——例如文学——背后包囊着的一系列评价标准,以及这些标准挤出去的“他者”。生活在异国他乡,这种“他者”的感觉几乎司空见惯——“潜移默化地觉得自己不重要”。我的语言究竟得多好,才能够在别人听我说话时,听不到“语言”这层外壳?也许这无法做到,也许这需要时间;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只是几乎直觉一般地了解一个事实:“想要做文学,终究要生理性喜欢才行”。
1
多语言者的困境
还在国内上学的时候,有一次听教授文学理论课的老师说起多语言者的困境。
她说:“最终所有的语言都背叛了我,包括母语。”
她用的词很重,“背叛”,用词夹着平静的恨。她说做文学到如今无法在各个语言翻译当中选择最好的词句,感到茫然无力。
就如同被诅咒了一样,曾经以为是命运馈赠的礼物到头来原是错谬。站在众多语言的交叉点上,知道了太多参差的可能性,于是再也无法抱守纯粹。每一步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到最后对于母语也终究问心有愧。
很多次,我都感觉到这如同被虫子啃噬的恐惧,让人直要在深夜惊醒。
我感觉自己自己被流放,被过去的一切,那些支撑我编织出了我的记忆的语言流放。
在平日里,我是一个外表正常的健全人,说着精心编制过的句子,写着语法正确的文章。看上去我仍然保有着相当的语言能力,母语的地位仍然无可撼动,然而无人得知其实我始终被无意识的语言淆乱折磨。
在清醒的时候我尚有余力维持各种语言系统的稳定,可每当深夜将睡未睡的边缘浮沉的时候,闪现出来的无意识话语不再是汉语而是法文,是夹杂了各种语言的英语中文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的杂糅体。
昏沉、无意识的时候我的大脑赤裸暴露在黑暗的危机里,那时我便无从抵抗。反映出没有掩饰的真相—我被巨浪切割得支离破碎。
这让我感到自己最终成为合成兽一样的人造怪物,我感到眩晕欲吐,像是被入侵。
哪怕表面上一切风平浪静,但如果我无法再写出从前的字句,如果我无法再像从前一样思考,那么我是否还是从前的自己?
无知是一种幸运,不必因为选择而疲惫,也不必失足掉落到语言和语言之间的缝隙当中。
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千疮百孔,我的语言千疮百孔。我在小说里写下的复合长句越来越多,长篇累牍,充满嵌套的从句和排比句。文字被一行一行地平铺开,我想往深处看却一无所有。
过往的山水最终还是晾干了,在我过于匮乏的言语当中,再也没有得以滋润文字的雨露。
偶尔偶尔,我仍然会翻开古文,仍然落泪仍然动容。但再也不能在高中坐在历史和语文卷子和练习册的山丘里,寻章摘句找出两三个令我如获珍宝的文常,合上书和朋友感叹“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或者”世上无数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
法语给予我对于自身汉语运用的新颖可能,但我并不开心。我始终站在不确定的浮冰上,怀疑这个词汇用得是否贴切,那个句子理解是否准确。
我的生命进程偏离了一条难以言状的古路,新的固然很好,可是终究人不如故。
当我看到从前的诗句,我感到深重的惭愧,我无颜以对。阅读得越多,却越空旷,越是失去而非获得。
2
在法国读文学,法语应该好到什么程度?
大三那年,教主课的TD老师说:我对外国学生的水平要求是,至少能够教授法国中学生文学课。
我倒吸一口凉气。
在国内和外教也好,法国交换生也好,交流我都没有任何问题,听纯法语讲座也能够理解80%。直到出国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别人都在将就我的语言水平讲话。
高中毕业之后,我考过了dalf c1想着来法国凑合能用了。真正到了法国之后,真枪实弹全包围沉浸式法语语境生活中,我才知道自己多么天真。刚来法国时法语水平完全不行,听课非常艰难,再加上当时年龄小没有处理生活杂事的经验,很多事情需要用电话交流加上电子杂音说话非常费力。
到法国的第一年,我几乎完完全全因为疫情封城被困在家里。第二年九月再回到巴黎时,突然感觉身边人说话都听得懂了,课也听得懂了。
再听正常语速的法语时,就像开了0.5倍速,每个词每句话都变得缓慢清晰。可能是因为暑假的休息让我不再在接受信息时因为过于焦虑而丧失理解能力。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语言能力在逐年提升,但一种环抱着我的不适感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能感受到,我身处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作为主体的环境里。不用开口我就知道自己到底有多么格格不入,如果接听者不有意付出耐心包容,我表达时输出的内容无论如何都比母语者更粗糙、有效信息含量更稀少。
我只有在让自己感到安全的环境里可以稍微敢于自我表达,可若身处的环境严苛、刻薄,我就会将自己封闭起来一言不发。我不确定信息接收者是否愿意倾听我的表达。
尤其是在注重效率正统的文学系,尤其是本科教育,其实并不像刻板印象中的外国大学鼓励学生自我表达,思维碰撞,这里的教学方式和任务主要是教人规矩。老师负责把最正统的文学脉络和规矩灌输给学生,至于学生有什么奇思妙想,这并不重要。日久天长,我也潜移默化地觉得自己不重要。
我通过凝视自己,把自己看成了他者,在瞬息万变的流水中从来没有找到可以安放自我的凹槽。文学系的语言能力要求,在很多时候是对咬文嚼字能力的要求。对于一个词一句话的分析,要敏感到如同能够分辨”留得残荷听雨声”和”留得枯荷听雨声”哪个更妙的程度。
中文我可以,但是法语不行。这需要很多很多的爱,对于母语深切的爱,和一种语言湿润的本能的,链接记忆、血缘和感性直觉天赋的爱意。在意识到这点之后,我明白了为了一个让我觉得体面的分数,我究竟需要付出多少代价。
这代价需要我重新搭建自我,搭建出一个真正能够爱上法语用词语句的自我来,如果不能从内部打碎一些事物,我如何把自己建起来?
如果我需要用数十年的努力构建记忆和经验才能爱上一门语言拥有在外语语境中本能的感受能力,说到底,我到底为什么非得爱一门不是我母语的语言不可呢?
我想回到自己的母语中去,可是被磨蚀过的原生语言系统也变得不再纯粹。我的用词、语序和思维方式都已经习惯了掺杂了西方语言表达,我喜欢写排比和长长的状语从句。
于是我又不得不去看古文,一边看一边感觉到温热的水流从心室里流出来,自然而然地、发自本能地。我不需要思考,不需要审美分析,不需要用力甚至不需要用心,它就像温热的血水从心脏里进出,循环全身。想要做文学,终究要生理性喜欢才行。

NEXT: 当一个00后开始怀念90年代
麦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