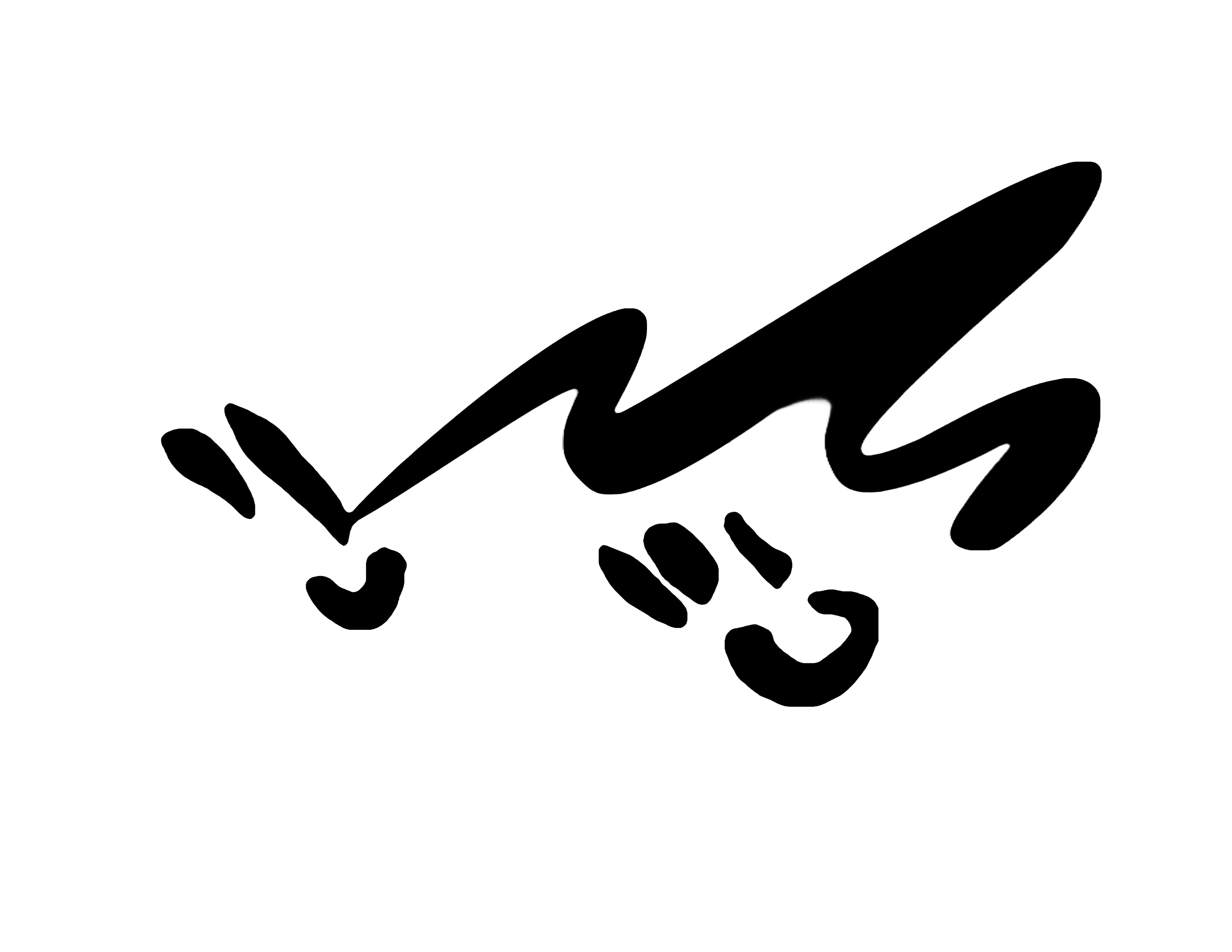南湖公园
王嘉宸
编者按:
在之前一次对王嘉宸的采访中,我曾问过他是否会在现实和想象几乎分开的前提下写作,作品内容又有多少来源于现实。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当时答道,于他而言,写作和现实是完全分开的:想象的世界很丰富、很有意思,而现实中,每天都做着几乎一样的事,枯燥而重复。他说,一篇他写的故事,最开始有百分之八十来源于现实,改着改着,可能最后就只剩下百分之十了。然而在读南湖公园的时候,有一种忽强忽弱的“梦核感”在我脑海中发酵。一开始我对它的来由不明所以,直到后来,我在他的自述中读到:“之所以给小说起名叫《南湖公园》,是因为我自己小时候经常在那里玩。记忆逐渐远去,变得模糊,一种声音,一种颜色,一种冬天空气里的味道,那是沈阳特有的味道。
在南湖公园的假山后面,有一个铁门,从那里就能通到东北大学的校园,我那时的家就在那里。现在,那个家已经不复存在,那些记忆的碎片变得不再真实,让人难以触碰,甚至连故乡都已消失。”怪不得,我恍然大悟。我的老家也在沈阳,这座城市灰蒙蒙的天、铁路、冬天时未结冰处滋滋冒着热气的湖在记忆中那么鲜明。“那是沈阳特有的味道。”在我看来,《南湖公园》携带着东北平原特有的梦核感。而这种梦核感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我们已经不在了。当我们的缺场成了另一种存在时,即便在想象之中,它也是那么鲜艳。这鲜艳是由我们强烈渴望寻根而生发的执着吗?我们或许仍然可以在虚构的角色身上找到答案。正如作者所说:如果我们假设,在主人公的旁边,现在有一个人拿着枪,顶在他头上,对他说:“如果你再不长大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你。”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主人公一定会躺在草地上,对着那个人说:“你就一枪崩了我吧。你崩了我,我也不愿意长大。”
每天早上,父亲都会去桥洞下面,捡火车道边散落的煤渣,运气好的话能装三袋,卖二十个大子儿。到了周末,他还会带上我和我哥。如果我捡的煤看起来不经烧,他就会弯下腰,从袋子里把它们一块块捡出来。父亲下腰的样子挺吃力。我常常想,大概每个人的骨头缝里都有一根发条,只是父亲那根很久没有上油,所以才会生锈。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家,住在一间仓库。仓库归国家管,但是一直没人看着,里面堆了很多空纸箱,上面写着机器零件的名称,还有老鼠在里面拉屎。每个月,父亲都会给火车站的老刘送一条烟,两瓶酒,于是老刘就让我们不交房租住在那儿。仓库有两间屋子,我们睡在紧里面那间,那儿放着两张木板床,没有大灯,但是有一盏写作业用的台灯。其实屋子里还有一股臭味,但是不注意就闻不到。味道的来源是仓库前面的垃圾山,夏天虽然挺臭,冬天盖上雪,居然十分好看。天黑后,我喜欢顺着仓库后面的水管,一直爬到屋顶上面,荡着腿往远处看。我老是能从远处的灯光里,清楚地认出南湖公园的那个大摩天轮。
九九年末,父亲出去捡煤,被一个火车司机当场抓住,扭送进铁路看守所。因为不知道他哪天会被释放,我和我哥一有空就去车站等他。我姑说,父亲犯的不是什么大事,最晚三十以前也该出来了。那个冬天,我哥没有留下一张自己的照片,但我仍清楚记得他的模样。他又高又瘦,头发长得老长,因为不爱洗澡,用手挤一下,可以挤出油来。我们在车站等着的时候,我哥喜欢把被煤染黑的雪捏成团,像扔手榴弹一样,甩到马路的对面。我则蹲在一架米格飞机下面,在心里默默数着从车上下来的乘客,其中有戴花头巾的老太,篮子里装着葱,还有吃冰棍的小女孩儿,但是从来没有父亲。我身后的那架飞机上,印着一颗闪亮的五角星,旁边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赠”,下面立着一个牌子,讲它多么的厉害,击落过多少架美国人的飞机。等得没意思了,我和我哥就沿着火车道遛弯,或者到野湖的冰面上出溜,看那些年纪大的人坐在板凳上钓鱼,其中钓得最好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者,只有一条胳膊,另一根袖管是空的,丢在朝鲜,在那之前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专业的手风琴手。有一回,他钓到的鱼实在太多,就分了一条给我们。我俩回到仓库,弄了半根萝卜,用它做了一碗汤,还在上面撒了葱花。那条鱼虽然小,但是很好吃,加了葱花以后,特别地香。事实上,那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鱼汤。
我哥喜欢踢球和嚼口香糖。一块草莓味儿的口香糖,他能从早上一直嚼到晚上,睡觉前粘到床头,如果第二天有甜味儿,还能继续嚼半天。虽然他嘴上说对女孩儿不感兴趣,但是我曾经抓到他偷看垃圾里捡到的卫生书,上面有张女性的人体构造图,标注了各个器官的位置。他最喜欢看的,是那张图的下半部分,那里的形状看起来,像一颗倒着的梨。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没有父亲管着,我哥竟然不去上学了。每天早上,我爬下床,到外面用脸盆接凉水拔脸的时候,他会故意用被子蒙住头,大声打呼。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白天都上哪儿去了。每天晚上,他都会像父亲一样,揣着二十块钱回来。他从没告诉我这个钱是哪儿挣的,但是我很快就闻到了他身上那股熟悉的味道,煤渣的味道。后来,他的班主任,一个说话声音很温柔的女老师,在操场上找到我,问我他去哪儿了。我就说,他得了一种很重的病,是不治之症,甚至可能会死掉。说着用双手勒住自己的脖子,做出咽气的表情。
那个冬天,天黑得比以往要早。我很少在放学后跟其他人玩,总是一下课就往回走。我费了老大的劲,才没让同学们知道我住在哪儿。每天,我都在一个被我称之为“我家”的路口跟他们道别,等注视着他们离开,再独自走回仓库。他们从来没就有发现我的秘密。在仓库里,我要摸黑走上两分钟,才能走到我们住的那间屋。我总是小心翼翼地绕过那些纸箱子,生怕打扰了老鼠们生孩子。这时,我就会想象自己不是在一间仓库里,而是一座图书馆,周围摆的也不是纸箱子,而是比我高了很多的书架,上面堆满了我永远也看不完的书,要搭梯子才能够得着。这种在黑暗中前行的感觉,就像是在和自个的影子玩捉迷藏。它大概是我唯一的朋友了吧。回来的路上,我总会经过一个巨大的广场,那里飘着许多旗子,有的写着“多买少买,多少要买,早买晚买,早晚要买”,有的写着“救孤济困,扶老助残”,有的写着“亲爱的朋友哈喽哈喽,百万的大奖在向您招手”。到了开奖日,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会在上面拿着话筒,叫那些幸运儿们走上主席台,开走停在边上的面包车,或是抬走摞起来的长虹彩电,并且问他们心里美不美(这就像是在问一个被自行车碾到的人脚趾头疼不疼)。开完奖,地面覆盖着老厚的一层彩票,让整个广场看起来就像是一张绣花的被子。即使在广场空了以后,我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穿着军大衣的老人,在雪里捡起这些散落的彩票,然后把它们放在路灯下,盯着上面的数字看。
父亲离开后,负责做饭的人就成了我哥,不过他只会煮挂面。于是,我们每晚都会变着花样吃面,有时候就着生蒜,每吸溜一口面,就啃一口蒜。到了周六晚上,我哥会用捡煤的钱,领我到独眼儿的饭馆吃饺子。他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吃法。饺子上来时,先吃五个,往盘子里加醋,吃五个,加酱油,吃五个,加辣椒油,再吃五个。这样的话,一盘饺子就可以吃四种味道。每天饭后,我哥都会靠在墙上做倒立,好像要把刚吃掉的食物再倒出来一样。如果没人打扰他,他可以一直倒立半个小时,甚至在倒立时打个盹。他说我太瘦了,像根苞米一样,要好好锻炼身体。当时我们养了一条白色京巴,年纪挺大,是父亲去年夏天在街上捡到的,身上的毛都掉光了。那之前,我还在纸盒里养过一只老鼠,有拇指那么大,长着两根教书先生一样的胡子,饿的时候会吱吱叫,用牙咬纸盒,甚至咬我的手指头。后来,它被一辆倒骑驴压成一张饼,粘在轮胎上,怎么弄也弄不下来了。我想管那条京巴叫“旺财”或者是“来福”,就是一般人会给狗起的名字,但是我哥坚持要叫它“艾森豪威尔”,他说那是一个美国总统。我问他美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美国人也要交社保吗?他说没什么关系,他只是觉着这个名字听起来挺洋气。后来因为念起来太长,我们就改叫它“老艾”。我用撕成条的纸堵住鼻子,打开台灯写作业的时候,老艾会安静地躺在我跟前,身体在暖光里轻轻起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点上台灯,屋里马上就变得暖和了。
寒假很快到来了,我并没有像答应父亲的那样考一百。我的数学考了七十,英语只有六十五。我似乎已经忘记自己也曾是一个好学生了。那时,老师们上课时最常提到的俗语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事实上,我唯一擅长的就是写作文。我的语文老师,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戴着啤酒瓶底一样的老花镜,把我叫到办公室。她跟我说,我写的很好,但是以后不要在考试里这样写,因为这样写的话,我可能有希望成为伟大的作家,但是永远也不会考进一所好的大学。我有时甚至会想,也许我应该像我哥那样,不去上学了。我常常想到父亲。我十分想念他。我老是觉得,早上一睁眼,就会看到他在煤炉那儿蒸粘豆包,然后抬起头,冲我招手。
一天下午,我和我哥从车站回来的时候,看到火车道旁的电线杆上贴着一幅画,上面是一头金色的狮子,前爪腾空,跃过一个点着了的火圈,下面写着:南湖公园,满洲大马戏,这个大年三十,我们不见不散。那张画好看极了,我们盯着它看了老长时间。后来,我四处张望了一下,看没有人,就朝着它的边缘哈气,然后小心把它从上面摘下来。我把画卷起来,像藏一把砍刀一样,把它塞在肥大的校服外套下面。我说,哥,我们要是能去看马戏就好了。他说,你说他们有狮子吗?我说,大概有吧,画上都画着了。他说,画上画的不是老虎吗?我说,我记得是狮子啊。他说,那保不齐是我记错了。我说,哥,等爸出来了,我们就去看马戏吧。他说,嗯,咱们一块去。
接下来的几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马戏。我有一块旧手表,没有表带,是父亲送给我的,后来差点被我弄丢了。因为当时我发现,我的校服兜破了个洞,如果往里面塞东西,过了段时间都会掉出来。睡不着的时候,我就躺床上,数父亲走后过去了多少天。我把你那块表拿出来,在黑暗中,盯着带荧光的指针看,好像这样就可以让它走得快一点。如果我哥翻了下身,我就把它藏到枕头下面,闭上眼装睡,然后那头狮子就一跳一跳来到我的面前,有点像大个的猫。它打了个哈欠,扭过头,对我眨嘛了两下眼睛,然后我就睡着了。
除夕前一晚,我被像流浪猫的声音吵醒了。我仔细听了听,忽然意识到,发出这个声音的并不是流浪猫,而是我哥。他正在被子下面哭泣。我在黑暗中睁开双眼,看到他像一只软体动物一样,轻轻抽动。这个发现让我有些后背发凉。我尴尬地躺在旁边,担心自己的呼吸声会打扰到他,时间像碗里的面条一样被拉长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猛然想起上次听到这个声音的场合。那是九二年,母亲走后的一个夏天。

母亲第一次走时我还小,但是我哥已经能记得所有的细节了。她拎着包从家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哥正坐在门口,跟几个邻居家的小孩儿玩啪叽。那个包看起来很重,母亲拎起来有些吃力。我哥问,妈,包里装的啥好东西,给我瞅一眼吧。母亲停了一下,突然转过身,递给我哥一个钢镚。母亲说,快,去买个冰棍儿吃,奶油味儿的那种,快去啊。我哥看了看钢镚上的国徽,抬头冲母亲笑了笑,发现她已经不见了。半年以后,母亲回来了。她给我俩各织了一件毛衣,蓝色的上面织着我的名字,红色的织了我哥的。当时父亲有点紧张,冲母亲笑了一下,想过去拉她的手,但是母亲没有理他。我看到,父亲居然像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几天后,一个晴朗的下午,母亲带着我和我哥去南湖公园坐天鹅船玩。她给我们每人买了根一块钱的烤肠,还唱歌给我俩听,歌叫《让我们荡起双桨》,好听极了。我们坐在天鹅船上,盯着岸边柳树后面的那些大楼看,它们看起来都十分遥远。母亲在家待了两个星期,再次不辞而别。那之后,每隔几个月,她都会回家一趟,看我俩一眼,每次回来我都特别开心,像过年一样。那时我老想着用一根绳子拴住母亲的脚,这样她就再也不会离开我了。后来就到了九二年,那年母亲走后就再没回来。从那时起,父亲变得沉默寡言,开始酗酒,我们也从老房子搬走了。一天晚上,他又出去喝酒,留下我和我哥在仓库。我记得,到了后半夜,我被相同的声音吵醒了。那个声音从窗户的方向传来,我则误把它当成了外面发情的流浪猫,但是现在我明白了,那是我哥哭泣的声音。
除夕那天,我哥起得挺早,他紧紧攥着两个拳头,在房间里面蹦来蹦去,又史无前例地洗了头,用梳子梳了梳,最后戴上了一条围脖。我们一起走到车站,在那里等了几个小时,期间只看到一个没腿的要饭的,一个卖冻梨的小孩儿,还有几个蹲在机翼下抽烟的下岗工人。到了中午,我们就着从家里带的撇拉丝,吃了几个花卷。花卷已经冻得咬不动了。我们喝光暖壶里的白开水,坐在飞机下面继续等着。我们等啊等,等啊等,但是并没有等到父亲。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一个拿照片的女人走过来,问我们有没有看到她的孩子。我看了一眼那张照片,里面有个穿红T恤的小男孩儿,留着寸头,看起来四五岁。照片下面有一行毛笔字,写得挺工整:寻找爱子,大名王海洋,小名毛毛,额头有疤,爱笑,对生人有礼貌,但是不爱说话,1994年于五爱市场走失,如有线索望知情人告知,当重金酬谢。我哥摇了摇头。她叹了口气,把被风弄皱的照片铺平,然后走过马路的车流,问对面亭子里站岗的警察去了。等她走远,我哥把嘴里的口香糖给吐了,捏在飞机下面的牌子上,跟我说别再等了,回家呆着吧。我没有动。他转过身说,你他妈的还在等什么?我没说话。他踹了我一脚,说,屁股给老子挪一下。我又站了一会,然后才跟着他走了。
我们走在火车道边,手插在裤兜里,踢着地上的雪,谁也不跟对方说话。后来,我哥到小卖部给我姑打了个电话,问她有没有父亲的消息。他说父亲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么久,我们十分想念他。我姑表示理解,同时也说自己什么信儿都没有,但她答应我们,明天一定去找人问问。然后,她又问我们有没有多喝热水,多吃蔬菜。我哥说谢谢姑,我俩过得挺好的,就把电话挂了。这时一道霞光从火车道的尽头升起来,看起来好像水流。
我突然说,也许咱爸永远也不回来了。
我哥让地上的雪块绊了一跤,继续往前走。
我说,哥,你说,以后再见到咱妈,你还能认出来她不?估计那时她已经很老了,脸上全都是褶子。
我哥停顿了一下。
那当然,他说。不管咱妈多老,我都能一眼认出来。
我说,你说爸没事吧?
他说,肯定没事,咱爸是啥人。
我说,那明天我们再去车站等他。
他说,嗯,明儿再去。
过了一会,我哥问我记不记得去年春节都干了啥。我说他妈的不记得了。他说他也他妈的不记得了。我又问他,你说,赵本山今年会不会上春晚?他说肯定会,因为年年都有他。我们又说起“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司马缸砸光”,还有“它为什么这么脆,它就是一盘大萝卜”。那些消逝的光阴,也好像都回到了我们面前,如树上的果子般任我们采摘。我哥说,这会他们要唱《难忘今宵》了吧。我点点头,几乎可以在耳边听见。路是那么长,下着那么大的雪。我想,父亲大概还要走好久,才能走到家吧。
走着走着,我们就走到了独眼儿的饭馆。窗户上贴着老大的红字,上面写着很多我们想吃但是吃不起的菜名。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里面的人喝酒,一团白色的雾气笼罩在他们周围,让饭馆看起来像个水缸,里面都是鱼,是人的身体,穿着人的衣服,但是长着鱼头。我转过头说,哥,你还有多少钱?我哥说,不用担心,够用,接着推门进去。我们坐下来,点了两瓶八王寺汽水,一盘饺子,猪肉韭菜馅,准备吃一顿没有父亲的年夜饭。不一会,独眼儿把饺子端了出来,又砰砰两声,撬开汽水的瓶盖。我看到他的狗眼儿歪着,盯着桌子上的辣椒油看。据说那只眼睛是以前他在厂里那会,被一颗从机器里飞出的螺丝钉弄瞎的,后来就换成了狗眼儿。我们拿起筷子,开始夹饺子吃,它们老是在盘子里出溜,好像长了脚,但我们还是把它们都消灭了。我哥走到柜台,掏出一把钱给独眼儿,然后从缸里挑了几块虾糖。离开的时候,我们还能听到独眼儿在后面说,大哥过年好,大嫂过年好。
走在黑暗里,可以看到人影在柳树林里发抖,看不清他们的脸,只能看到他们手里燃烧的香烟。路边有几个女孩儿在不住地跺脚,虽然很冷,却穿着很短的裙子和薄薄的丝袜,脸上画着浓妆,好像在等人。我哥像递香烟那样把兜里的虾糖掏出来,给了我一块。我把包装拆开,糖含在嘴里,慢慢用牙咬,是甜的,让我有点想哭。火车道对面传来礼花弹的声音,像山谷里在打雷,但是很快,一切又安静下来,路上只有我俩。我打了个喷嚏。我哥把他的围脖摘了,扔给我。他说,你快把它给我戴上。我用校服袖子抹了抹鼻涕,大声说,我不要这破玩意儿。我哥没说话。过了一会,他拍拍我,问我有没有听说过爱斯基摩人,我说没听过,他就开始跟我说,爱斯基摩人住在北极,有一种在雪地穿的鞋,看起来像踩着一对羽毛球拍,走在雪里,就像是走在平原上一样。我听到他的描述,脑子里涌现出几个踩着球拍在雪上奔跑的人,突然很想笑。我感觉我笑得肚子都疼了。垃圾山前有一个孤单的男孩儿,正在放礼花弹,他点着它,拉下棉猴的耳朵,用手捂住。我们没有打扰他,绕过垃圾山,来到仓库跟前。大门敞开着,冷风不住往里灌,我能听到老艾在叫唤,但是后来好像叫累了,就没动静了。我以为是父亲回来了,身体忍不住颤抖起来。我们在纸箱间穿行,我哥从兜里掏出打火机,举到面前,火光照亮了他的黑眼仁,还有他下巴上几根很短的胡子。我们站在屋外,看到里面有灯光在晃动,然而打开门,出现的却是两个戴大盖帽的人,一个头发已经灰了,另一个还很年轻,都拿着那种大号的手电筒。一个在翻柜子,把里面的东西扔到地上,另一个在用手摸我们的被子,并且把它掀开,看下面有东西没有。
这时他们看见了我们,年纪大的那个往年轻的身边凑了凑,交代了几句,就站到窗边抽烟去了。年轻的走过来,问我们有没有身份证,家里大人在哪儿。我把一只手抬起来,挡住脸上手电筒的光。年轻的有点不耐烦,说,你们是哑巴?我哥说,叔叔,你们过年都不休息的吗?年轻的没有回答,说,是谁允许你们住这儿的?我哥说是火车站的老刘。年轻的说没听过这么个人,转头问年纪大的。年纪大的停了一下,说,老刘?然后摇了摇头,在窗台上弹了两下烟灰。我能听到老鼠叫,还有外面放炮的声音,每放一下,我就打一个激灵。年轻的把帽子摘了,在我哥头上砸了几下,问他是不是在撒谎。我哥发誓他说的是实话,真是火车站的老刘让我们住这儿的。年轻的不说话了,好像是在思考如何处置我们。这时年纪大的把烟掐了,绕过我哥,对我说,孩子,你知不知道,一个人拿了别人的东西,这个叫什么?我说,叫什么?他说,叫小偷。小,偷。我想说我们不是小偷,但是没有讲出口。他又说,社会上有一种人,自己不劳动,专门薅社会主义的羊毛。你知不知道,这种人是哪种人?我想了想,好像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点点头,语气缓和了许多,说,你们还小,什么也不懂,现在大晚上的把你们赶走,也不符合我们的政策,但是明天早上,你们必须得从这儿搬走,明白吗?说完他们就离开了。
过了一会,老艾不知从哪儿跑了回来,闻了闻我裤腿上的雪,用舌头舔了两下。我踢开它,到外面的雪地里撒了泡尿,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我哥脸朝下躺在床上。他又哭过了。我把台灯从地上捡起来,用校服擦了擦。我想,如果它摔坏了的话,我可以重新修好它,但令我没想到的是,它把整间房间都照亮了。我把藏在墙缝里的全家福抽出来,塞进裤兜,又拿了几本作业本,两支削好的铅笔,几双厚一点的袜子,还有早上吃剩的半个花卷,然后坐在床边,看着手表上的指针。我哥擦了擦眼睛,什么都没拿,两手空空地站起来,朝着外头走去。我站起来说,哥,要不等明早再走吧。我哥没有理我,在黑暗中走了两百米,然后推开仓库的大门。外面又下起雪来,而且越下越大。我说,要睡外头吗,就是挺冷的,要不要像爱斯基摩人一样,搭个雪屋?我哥把头埋在衣服里,一句话也不说,扎进大雪,我赶紧追上他。走了不知道有多久,我说,哥,咱们这是要去哪儿?我哥说,去南湖公园。我愣了一下,不再说话,默默跟在他后面。我回过头的时候,看到老艾正远远地跟在我们后面。过了一会,我抬头看到了摩天轮,在夜空中,看起来就像一条很大的珍珠项链,只不过是已经熄灭的项链。

公园的大门上锁了。我们来到围栏外,我哥弯下腰,让我踩着他肩膀,我爬上围栏,伸出手把他拽上来。正要往前走,老艾突然叫了几声,追上来,跟着挤进了围栏。我哥看了看它,把它捡起来,抱到怀里。公园里一个人都没有。我们经过旋转木马,碰碰车,还有三个芭蕾舞女孩儿的塑像,来到卧波桥,在那儿能看到许多搁浅的天鹅船。夏天湖水是绿的,但是现在一半冻成冰,没冻的部分滋滋冒着热气。小路边有盖着雪的长椅,上面有人坐过,像压进生日蛋糕的脸。马戏团大概在公园的很里面,我们找了一会,没找到。我意识到,有可能压根就没有这么一个马戏团,这一切都是我瞎想出来的。这时,一个熟悉的音乐从“丛林小火车”的后面传来,是《铃儿响叮当》,有点像我小时候听过的八音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年三十的晚上,这里却在放着外国人的音乐。我和我哥走过去,看到一座破旧的帐篷,旁边的牌子上写着几个字,已经快看不清了,好像是“满洲什么戏”。我的心砰砰地跳了起来。来到帐篷后面,我哥指了指帆布,上面有个洞,差不多一个咸鸭蛋那么大。他放下老艾,伸长脖子往里面看,柔软的雪花落到他的肩上。帐篷里又传来了音乐,我想里面一定在表演着什么精彩的节目。我等不及了,就问我哥看见了啥。他没吱声,影子在地上一动不动。我大声说,我也想看,然后捏了个雪球,朝他扔去,雪球在他后背留下一个白点。他晃了晃,扭头看着我,像是刚刚睡醒。我说,我也想看,然后一把将他拉开。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身体特别轻巧,直接被我甩到了雪里。我没有管他,把脑袋凑了过去。里面什么都没有。我感到十分困惑,转身看着地上的我哥。我哥让我再仔细看看。我有点怀疑,但还是把脑袋凑到跟前。那里一片漆黑,只能听到那个熟悉的音乐,但是不一会,梦里的场景都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我大吃一惊,揉了揉自个的眼睛。我哥问我看到了什么没有。我没有回答他,继续看着,直到耳边什么都听不到了,只剩下微弱的呼吸声。这个声音好像来自地底,但也有可能,它不来自任何地方,而是一直就在那儿。我终于看到了狮子。
2021年十二月 一稿
2022年三月 二稿
2023年二月 翻译
2023年十二月 三稿

NEXT: 雪山上的伊卡洛斯
苗之朴
wushushan9@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