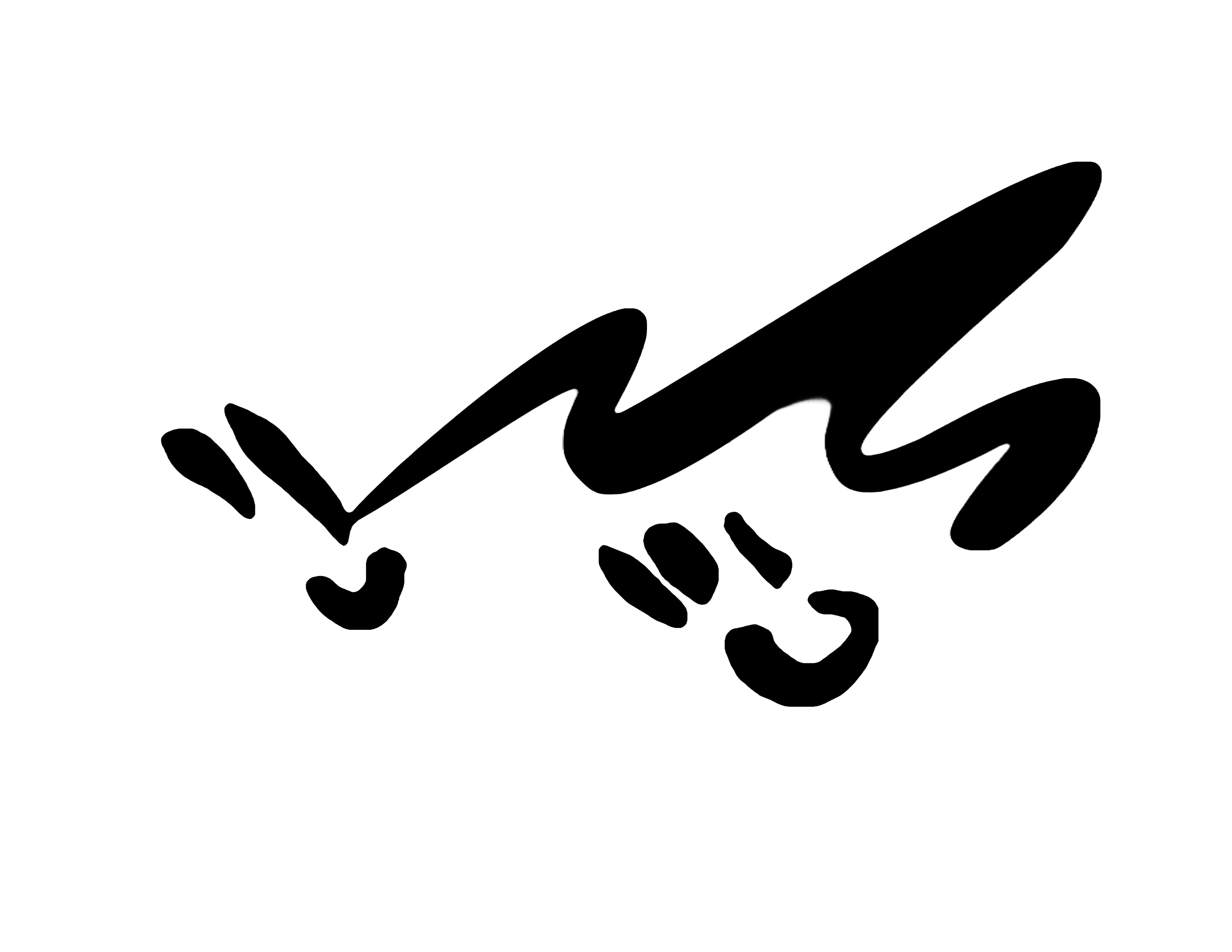雪
王嘉宸

编者按
王嘉宸你好,
第二次看完《雪》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哭。很久以前的我以为世界会一直、一直不停地进击下去,直到高中的时候这个想法全部化为了泡影。如果没有爱,进击的人就像油灯,某一刻它一声不响地,就灭掉了。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精神处于极其低落的状态。就像小宇或小惠那样,我习惯去北海公园的湖边,一圈一圈地走,直到不那么难受为止。北京缺水,所以总觉得和气候也有关系:是我的内在都全部干掉了,当时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一次次往北海跑,没有新的生活,每天看以前的相册,然后从那里面挖掘一些久远的余温,供给自燃。读完《雪》我很想哭,可能是因为想起平安渡过了自杀情节后,我就再也不敢翻相册了,每每不小心滑到时间久远的部分,就干脆直接关闭掉它。《雪》让我想起了这件事。或许是因为没有那些回忆的媒介,我才能抛弃一个被用光、被干涸的自己。所以,可能小宇和小惠的信是我能想象到最最恐怖如斯的温和。难道不是吗?一个人翻开相册,看到一个久远的年若温柔的人,长得很像自己,还看到没有去世的亲人、朋友,在信封上的嘴唇印,细节到那时看完某部印象深刻的小说后,假装生活是其内容的延续……那些本该更彻底的、被明快地删除掉的东西,居然到头来还是删不掉的鲜艳耀眼,这让我想起斯佳丽说的,别回头,别回头。“我们还有明天”。我总觉得说这句话的声音一定是颤抖着的,因为回头的代价那么高,那么让人心碎,回了头就不得不发现,原来有一种纯粹的贫穷是没有任何可以换回的:从没发现到发现笔友是个女孩;从幻想,到见到第一桶被装进保温杯的雪。知道了就不能不知道了,没有什么能换回懵懂,没有什么能换回一个曾经的还没被填满的人。如果换作是我,最后,我也会说:那么去唱歌吧。如果不唱的话,还能怎么办呢?
但那天读完《雪》之后,我在微信小号里写道:“世界上有写小说的人真好。晚上读了朋友的小说,我就像因为在冬天吃了一颗苹果后变得柔软的人。感觉所有悬在什么中间的东西都轻轻地贴在了一起。”我说你是我的朋友,但其实我没见过你,也不了解你。这件事挺神奇的。我像吃了苹果后变得柔软的人,这也绝不是因为那种读久远来信的恐惧感,都因为这篇故事而被轻轻克服。反倒是,我看到了那种恐惧。我的目光,穿过小宇和小惠的信,穿过南湖公园,穿过沈阳,我的童年的一部分,同样被葬在沈阳的公园里的亲人,最后像一只蝴蝶一样,安静地落在了它微微颤抖的身体的上面。
鳄鱼
在我的少年时代,有长达四年的时间,我都在给一个女孩写信。起因是学校里组织的一次笔友活动,由北方学生写信给南方学生,再由南方学生回信给北方学生。活动配对按照性别,也就是说,男孩写给男孩,女孩写给女孩。然而,在写第一封信的时候,我不小心在门牌号后面多加了一个零,把信寄给了一个陌生人。按理说,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可是那个陌生人居然回信了。信中说,他跟我年纪相仿,也在上初中,欢迎我继续给他写信,并且在署名的地方画了一个戴墨镜的小人儿,鼻子下面留着胡子。我十分激动,立刻给他写了一封回信。一开始,我以为对方也是个男孩,就在信的开头也画了一个留胡子的小人儿,他并没有纠正我。后来有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就用手电筒照天花板玩。过了一会,手电筒没电了,四周一片漆黑,一个念头忽然从我的心里闪过,那就是一直以来,我都是在跟一个女孩写信,一个伪装成男孩的女孩。在下一封信里,我给小人儿加上了长头发,头发上面还画了一朵花。一周后,她回信了,语气十分惊讶,问我是怎么发现的。我说是一种直觉,同时问她介不介意把真名告诉我。她说完全不介意。她叫朱小惠,朱元璋的朱,阮小二的小,山口百惠的惠,叫她小惠就可以。
很快,小惠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她告诉我,每隔一段时间,她就要去医院住几天。如果没有及时回信,不是因为她不想写,只是因为她还没有看到。我问她为什么要住院,是生了什么病吗。她说,她确实生病了,但是这种病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里面的。好的时候,她就跟正常人一样,该吃吃,该喝喝;不好的时候,她就完全变了一个人,连她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我在回信中表示了理解,安慰她没关系,还让她好好养病,多吃苹果,因为吃苹果对身体好。
二〇一〇年的夏天,我在中考中发挥失常,去了全沈阳最差的一所学校。其实也说不上是发挥失常,只能说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全班倒数的水平。收到成绩单后,我爸喝了不少酒,趴在饭桌上睡着了。我妈则给我发来一条短信,说她希望自己从来没有过我这么个儿子。离家那天,我用铅笔写了张纸条,搁在饭桌上,上面写着:“对不起,爸爸妈妈。我会继续努力的。落款:您们的儿子。”然后回到房间,背起书包,独自去了车站。书包里面装着我的全部家当:几张老电影的盗版碟,一个随身听,一本《爱捉迷藏的小男孩》,几个苹果,还有一摞小惠写给我的信。
在新学校,我仍然跟小惠通信,尽管我们从未见面。我跟她讲了很多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比如说班上的一个男孩,用钥匙把另一个男孩的眼睛弄瞎了,进了少管所,或者是一个我认识的女孩失恋了,得了抑郁症,最后从学校退学,从此不知所踪。不知道从哪一封信开始,她会在信纸背面,留下自己的口红印。她的嘴巴很小,上面有一些细细的纹路,像树的年轮一样。有一次,她写到自己从来没有见过雪,我就跑到操场上,捧起一把雪,装进一个保温杯,然后寄给她,告诉她,这个白色的,柔软的,甚至有点温暖的东西,就是雪。再后来,我跟学校里的一个女孩谈恋爱了。那个女孩听说我一直在跟另一个女孩写信,就趁我不在,把我书桌里的信都撕碎了,扔进垃圾桶,又被我捡出来,小心地用胶带粘在一块。打那以后,我开始偷偷写信,然后趁她不在的时候,把信投进校门口的邮筒。一个月后,她发现了,在我的寝室里大哭一场,然后提出分手。我同意了。
二〇一三年,高中毕业的那个夏天,小惠突然没有了消息。我给她写了十多封信,无一收到回复。我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坐火车去上海找过她。她搬家了。我们从此失去了联系。

小惠你好:
对不起,我字写得确实有点难看,不过我已经在努力练习了。真的。你的照片我已收到。你问我自己长得怎么样,我觉得,你简直长得太好看了。你是我见过最最最最最最最好看的女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有明亮的眼睛,但是并不能真的看见,因为当一件珍贵的东西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却不觉得那是珍贵的,只有当那件东西不见了,他们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你提到的那个男孩,他不喜欢你,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他瞎,知道不?你比他们都好,他们都配不上你。
小宇
附:我也在信封里放了一张自己的照片。

小宇你好:
我收到了你的来信,拿在手里,信封还是热乎的。你说的对,不光吃饺子要吃热乎的,看信也要看热乎的啊。我感觉,它就像是一个心脏,里面装着的东西,还在砰砰直跳。谢谢你的安慰。昨天放学,我值完日,又在走廊里看到了他。他的眼睫毛真的好长啊。我从来没见过谁有他那么长的眼睫毛。你知道吗?他现在有了一个新女朋友,是别的班的,长得很好看,大概比我好看多了吧。我当时很难过,现在已经好多了。我有一个妹妹,叫小萍,刚上初中,跟我长得很像。我们还是小baby的时候,后脑勺那里,都有一小块是软乎乎的。长大以后,我的后脑勺就变硬了,不过她的还一直软乎乎的,你说奇不奇怪?我从来不担心其他孩子在学校里欺负她,因为她打架很厉害。她已经换了三个铅笔盒,前两个都被砸坏了。有一次,她回家的时候流着鼻血,脸上还青了一块。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班上有男孩往她裙子上抹胶水,她就跟人家打了一架,最后把他给打哭了。我很爱她,我也很爱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很好很好的人,可是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都过得很煎熬。你说,活着为什么这么累呢?
小惠

小惠你好:
我明白你的意思,真的。每天放学,我都不想回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家是一个特别压抑的地方。我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判给了我爸,我妈嫁给一个药厂的厂长,过上了她梦寐以求的生活。我爸对我很好,但是我跟他没什么话说。他的手很巧,像那种弹钢琴的人一样。我小的时候,他会用小刀做木头玩具给我玩,比如说毛主席的头像,天安门的城楼,还有四个轮子都能动的红旗轿车。现在,我已经不记得这些玩具都放在哪儿了,但它们曾经是我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
有时候,我会背着书包,去北陵公园里面坐一会。以前我常和我爷在里面溜达,现在他已经不在家了。他去了养老院,那里住的都是和他一样的老人。那些老人,有的还能站在院子里晒太阳,有的就只能躺在床上,靠别人喂饭。我不开心的时候,就会到公园散步,绕着北陵湖,从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走到这头,然后我就不难过了,你也可以试试。靠北陵公园西门,有一棵大松树,是皇太极死时种的,到现在已经几百年。树干极粗,很多年前,有许多相爱的男孩和女孩,把自己的名字小心地刻在了上面,后来历经风吹日晒,字迹逐渐模糊,和树干融为一体。有时候,我会坐在那儿喂喜鹊。喜鹊是我最喜欢的一种鸟。喂喜鹊的时候,我总能看到一个穿军大衣的老头,佝偻着腰,坐在离我不远的树下。他看起来和我爷一样老,所以一看到他,我就想到了我爷。他嘴里一颗牙都没有,却在吃一根糖葫芦,而且把它都吃完了。你说,一个牙都没有的人,是怎么吃完一整根糖葫芦的呢?
我的很多亲人都埋在北陵公园。我奶是几年前埋的,我太爷和二爷是“文革”时埋的,就埋在一颗松树下面,现在已经找不到是哪棵了。我太爷原来是说书的,可以把一整部《岳飞传》都背下来,但是老了以后得了痴呆,连自己叫什么都不记得了。那时,我爷常常背着手,在公园里走啊走,走啊走,边走边说,等他死了,也要在北陵公园找一棵树,然后把骨灰埋在下面。一家人,不就是图个整整齐齐吗?我爷心脏不好,可是我还年轻,我的心脏像远洋的大船一样结实。如果可以,我想把我的心脏分一半给他。但是我爷说,人总归是要老的,就像叶子会从树上落下来。但是人老了,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很快,他就可以知道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了。在另一个世界里,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痛苦了。
小宇
附:你看过《爱玩捉迷藏的男孩》吗?

小宇你好:
我看你的信,居然看哭了。我是不是一个爱哭鬼?你说人老了,就像叶子从树上落下来。我只有十六岁,可是我觉得,我的生活也像叶子一样。我给你写信的房间很小,但是我心里的世界很大很大,就像宇宙那么大。听说东北的糖葫芦和我们这边不一样,是真的吗?是不是因为有冰气,吃起来凉丝丝的,和冰棍儿一样?我这里很热,总是下雨,每天晚上睡觉都要开窗户,而且有很多蚊子。你说的那本书我没有看过,但是我妹很喜欢看。她枕头下面就有一本,是从图书馆偷来的,已经快被她翻烂了。书皮上面,画了一个没有影子的黑色男孩,躲在门后头,小心地踮起脚,把脑袋凑近猫眼,往外面看。这里有七本书,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你也可以去看看。分别是:霍尔顿·考尔菲尔德《中央公园的鸭子》;阿列克·谢尼古拉·安东诺夫 《悲伤的男人们和女人们》;L·曼宁·瓦因斯《四个爱斯基摩人的最后十五天》;弗吉尼亚·蒂普顿《七根火柴的光》;鲁迅《杨贵妃》;哈克贝里·菲恩《密西西比河漂流记》;瓦伦蒂诺·柯里昂《中国瓷器》。
小惠
附:我给你买了一个随身听,也装信封里了。你喜欢听音乐吗?听我的,别再用带线的信纸了。

小惠你好:
我到新学校了,接下来这段时间,请把信寄到信封上面的这个地址。你敢相信吗,我的宿舍本来能住六个人,但因为学生没招满,只住了两个。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阿廖沙。他喜欢看一本很厚的俄国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叫阿廖沙,所以我们都叫他“阿廖沙”。除了这本俄国小说以外,他就不怎么看书了,但是他人很好。我看书的时候,他怕吵到我,就会惦着脚走路。刚来学校那几天,因为食堂太难吃,我和阿廖沙就翻墙去小卖部买吃的。回来的时候,宿管躲在树林里,听到有动静,就用手电筒照我们。有一次,我们两个马上就要被抓到了,是阿廖沙站起来,主动暴露了位置,我才没有被发现。还有,我在宿舍里偷偷养了一只流浪猫。一开始我以为它是黑白相间的,给它洗了个澡才发现,它身上的毛全是白色的,像雪一样白。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它一直跟在我后面,怎么赶都赶不走,后来,我就只好把它藏在校服下面,带回了宿舍。它是个哑巴,不会说话,但是喜欢在我看书的时候拿后背蹭我,晚上就睡在我床底下的纸箱子里。那是我给它做的小窝。它的嘴很叼,只吃双汇的火腿肠,食堂的饭一口不动。等再攒点钱,我就去给它打疫苗。我准备叫它“汤姆·索亚”,因为他们都是黄毛。你说这个名字怎么样?你妹可太有意思了,再多跟我讲讲她的事。
小宇
附:这里下雪了,而且下得很大,像鹅毛一样。你听说过这个比喻吗?鹅毛大雪。到今天我才发现,原来雪花真的跟鹅毛一样。

小惠你好:
我一个月没吃午饭,终于攒够钱,把你说的那些书都买了。这就叫骑自行车逛酒吧,该省省,该花花。我读了其中的一本,没有读懂,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书的问题,而是我的问题。我会继续努力的。上次你提到你有个妹妹。你知道吗?我也有一个哥哥,在我很小的时候去世了。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冬天。他在冰面上出溜玩,看到一个小女孩掉进冰窟,就下水把她给救了上来。因为在水里泡得有点久,他回家以后得了重感冒,但是谁都没有告诉,起床了还坚持上学。那天傍晚,回家路上,他突然觉得很难受,有点喘不上气来,打算到旁边的雪地里休息一会,结果在雪里睡着了,再也没有醒过来。我爸和我妈就是因为这件事,才不跟对方说话了。我们家的电视机上,常年挂着我哥的遗像,下面还有一个盘子,里面放着两个苹果,上面有我爸用记号笔画的笑脸,他说我哥活着时特别喜欢吃苹果。看我哥的照片看久了,我觉得自己好像也认识他了,而且跟他很熟。没事的时候,我就把那张遗像拿下来,抱着他说话,跟他讲我喜欢上了班里的哪个女孩,期末考试又有哪道题不会做,上课的时候偷偷在桌子底下,看的是什么书。
小宇

小宇你好: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从来没有见过雪。这是真的。雪摸起来是什么样子呢,应该跟棉花差不多吧,软绵绵的。我不知道跟没跟你说过,每周六早上,我都会去坐同一班公交车,有时候坐几站就会下车,有时候一直坐到终点站,再从终点站坐回家。我常常在车上碰到一个女孩。每天早上,她都会在我家前面那一站上车,然后坐到我旁边。她的头发很长,带点羊毛卷,后面扎着个蝴蝶结,怀里抱着一双白色但是磨破了的舞鞋。久而久之,我就很想认识她,但是每次我想跟她聊聊天,说几句话,她都不搭理我,只是看着窗外。外面有什么好看的呢?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明白,那个女孩是一个聋子。这样说可能不太好,我的意思是,她的耳朵,完全听不到任何声音。我说这个的原因是,当我觉得自己不被理解的时候,有没有可能,那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我自己的问题呢?是不是因为,我没能真正地倾诉自己的内心?还是说,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地理解任何人?
我妹喜欢打篮球,也喜欢踢毽子,我喜欢在家里看书。前一段时间,她用剪刀把自己的头发剪短了,和男孩子差不多。她不喜欢别人跟她做一样的事情,穿一样的衣服。有一次,我在楼下的垃圾桶里面,看到了她新买的运动鞋。我把鞋从垃圾桶里拿出来,问她为什么要扔。她说是因为班上一个女孩看了她穿那双鞋,觉得好看,就也偷偷买了一双,穿到学校。她看到后,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如果她有的东西别人也有了,那么这件东西就不是独一无二的了。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俩在外面玩,如果很晚还不回家,我妈就会打开窗户,用一个很亮的手电筒照我们。我知道这是她在叫我回家,就拉着我妹回去,但是她说还没玩够,要等玩够了再回去。真是拿她没办法。就在今天,我妹说,她跟班上的男生打架,第一次输。她觉得很丢脸。我告诉她,你不能再跟那些男孩打架了,因为他们以后只会变得越来越强壮。她想了想,抬起头说,是不是长大了以后,女孩就打不过男孩了?我告诉她,也有可能,这一切只是世界的表象。她说,那什么才是世界的本质呢?我说,本质就是,你要把那些和你打架的男孩,还有其他所有的男孩和女孩,都想成自己的兄弟姐妹。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在很久以前,都是另外一个人的兄弟姐妹。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里面的孩子,住在一个温暖的山洞里,并且深深爱着对方。后来,过去了太久的时间,大家都把自己是谁给忘记了。但是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走在路上,满身尘土,会突然认出对面那个人的面孔,想起那些遗忘的记忆,然后我们就会拥抱在一起,庆祝这一切。
我在信封里塞了两百块,是我妹帮我从我妈钱包里偷的,拿去买点好吃的吧。不吃晚饭对身体不好。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可喜欢吃大白兔奶糖了。
小惠

小惠你好:
我爷去世了。他走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几乎是在一瞬间,他的个子变得很小,小到我都快看不见了。我们像他希望的那样,把他埋在了北陵公园的一棵松树下。他留下来的东西很少,其中有一副碎掉的眼镜,用报纸包着,看起来很旧了,我把它跟骨灰埋到了一块。回到家,我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故事。故事里也有一个“我”,“我”的爷爷也死去了。“我”一个人在北陵公园里面走着,前面的路突然消失,从树林深处走出一条队伍,队伍里都是老人,有的戴着勋章,穿着中山装,有的举着红色的小本子,两旁是一些穿得花花绿绿的,长着狐狸尾巴的人,正不住地敲锣打鼓。这时,“我”在队伍中看到了“我”的爷爷。“我”叫了他一声,他回过头,像不认识“我”了一样。“我”说,爷爷,你怎么会在这儿呢?他看了“我”好半天,然后说,孙子,是你啊。“我”说,是我啊,爷爷。你在这儿忙什么呢?他说,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呢?“我”说,爷爷,你跟我回家吧。他说,孙子,这里就挺好,我不走了。你一个人回去吧。说着他摆摆手,回到了队伍里。他们越走越远远,消失在松树林的深处,像一只只萤火虫。
写完这个故事,我感觉,它好像真的发生过一样。就像你在小说里描写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并不是那个真实的地方,只是镜子里的它。可是有一天,你发现你写的那个地方,影响了那个真实的地方,直至最后取代了它。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谢谢你给我的钱,我买了好多的大白兔,都放在床头的月饼盒里。晚上看书看饿了,我就拿出一颗,撕开包装,含在嘴里。你妈没有发现吧?小时候,没什么机会吃奶糖,只有过年了,我奶才会在包饺子的时候,挑一个,把糖放进去,谁吃到了,就可以走运一整年。有一年让我给吃到了,真甜啊。你不是问我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吗,把耳朵凑得离信纸近点,我偷偷告诉你:我想当一个小说家。你喜欢看小说吗?这还要感谢你跟我说的那些书,我觉得, 我现在能看懂一些了。
对了,阿廖沙告诉我,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孩。我问他是谁,我认不认识。他说我见过,是在学校附近的马路边遇到的,长得很瘦,穿着白背心,手臂上有烟头烫的伤疤。当时她站在街边招呼我们进去坐,我们两个都没有进去,不过阿廖沙一直回头看她。打那以后,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女孩住的出租屋,没钱了就打电话跟家里要。今天,阿廖沙又去找她了。他从小猪存钱罐里拿出两张钱,偷偷溜出了学校,半夜才从窗户翻回来。我问他怎么样。他停了一下,然后告诉我,他觉得自己爱上那个女孩了。还从来没有人,像她那样那么温柔地碰过他。他说,在出租屋的黑暗中,他和那个女孩一起躺在床上,而在她洁白的腰上,系着一根细细的红绳。于是他就问女孩,为什么不把它解下来呢。然后女孩就抱着他说,那是因为啊,有一天,她会碰到一个她爱的,也爱她的男孩。到那个时候,她就可以把这根绳子解下来,抛下这个屋子,还有这个屋子里放着的一切,跟那个男孩私奔,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过上崭新的生活。但是在那一刻到来之前,她要一直系着它。
那天晚上,上铺一直传来轻轻抽动的声音,听起来很像哭声。
小宇

小宇你好:
谢谢!!!(一个大大的爱心)今早我收到了你寄的保温杯。原来保温杯里的雪,也可以是暖的。那个包裹外面缠得严严实实的,像一个大粽子一样(原谅我差劲的比喻)。昨天我在公交车上看到了两个尼姑,一个老尼姑和一个小尼姑,那个小尼姑的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大概是她的孩子。你说有意思不?最近我总是咳嗽,一咳嗽就整宿睡不着觉,而且有时候能咳出血来。不过别担心,医生说不是大问题,休息好就可以康复了,还说我一看就是那种很健康的女孩子。能多和我说说你的小说吗?它们都是怎么写出来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海里有这样一幅画面:你坐在桌子前,手上拿着一支笔,就像一个家伙站在田野上,等着风来,等了很久都静悄悄的,这时一个好句子突然从面前飘过,你伸出手,赶紧把它抓住,揣进兜里。你听说过凡高的靴子吗?某天早上,凡高画了一只靴子。在他把画笔放下的那一刻,这只靴子活了,有了自己的世界。于是画的另一边,就有了一个满面尘土的农民,他每天穿着这只靴子去劳作,晚上睡觉前再把它脱掉,随意扔到床底下,如果鞋底破了洞,他还会补一补,用胶粘好。这只靴子变得如此真实,我们甚至可以闻到它的臭味儿,用手一蹭,还能蹭到鞋面上的灰尘。其实,不仅画画是这样,所有的艺术都是这样。当小说家写出一篇小说,他就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真的有人伤心,有人哭,有人死去。你相信信念的力量吗?据说,一个恶人临死前悔过的善念,就像山谷里的一道闪电,足以弥补他之前犯下所有罪行的总和。你相信吗?我常常想到,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平行宇宙里,会不会有另一个我,一个更勇敢的我。她在某一个时刻,做出了和我不一样的选择,过上一种和现在的我相比,截然不同的生活。如果那样该有多好啊。
小惠

小惠你好:
从上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你最近状态好多了。我真为你感到高兴。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很担心,如果以后见到你的话,会认不出你来。你能再给我寄一张你的照片吗?最好是最近几个月的,我想知道你头发有没有变长,样子有没有什么变化。对了,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不过我喜欢的东西她都不敢兴趣。她说,她以后的梦想是挣很多很多钱,住上一个大房子,然后可以吃很多好吃的,买名牌的衣服,还有很多人伺候她。她问我喜欢什么,我说我喜欢写小说,她愣了一下,没有说什么。然后我们两个就坐在那里,看着外面的天空慢慢变黑。这个时候,我感觉到她的手,离我的手越来越近,直到我们的手指,都快要碰到一块了。我觉得很尴尬,就吹了一会口哨,还问她要不要吃大白兔。她说大白兔会粘住她的牙套,到时候弄不下来。那天晚上,我们接吻了。然后她哭了,她问我是不是真的喜欢她。我说当然喜欢,可是我觉得,其实我并不是真的喜欢她,而是为了有个人可以喜欢而喜欢她的。因为我有一个真正喜欢的女孩,却没有办法告诉她,只能远远地看着,希望她过得好。最近我写了三个故事,把它们都送给你吧。你是我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读者。
1)一个男孩,从小就没有了妈妈。他的爸爸是一个身材高大,满脸胡子的男人,每个秋天,都会跟一艘大船出海,第二年春天才归来。于是,男孩总是沿着通往茅草屋的道路,独自在沙滩徘徊。后来,一个打渔的老人告诉他,如果他在海滩的沙子里找到一百个鲨鱼牙齿,那么就可以实现一个愿望。那样我的妈妈就可以回来了吗?他问。当然可以了,打渔老人说,你想要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我只有一个愿望,男孩说。那就是让我的妈妈回来。
2)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也是一个男孩。他不像第一个故事里的男孩一样,住在海边的茅草屋。他的家是一座华丽的庄园,有许多仆人,还有一个美丽的母亲。然而有一天,他的母亲,在庄园附近的隧道里走丢了。男孩十分勇敢,拿着玩具弓,带上自己用胶水和羽毛做的箭,还有一个小小的矿灯,到里面去寻找她。五十年后,男孩变成了一个老人,长出了白头发,隧道终于到底了。那里除了一面镜子以外,什么也没有。他发现,在镜子的另一面,走丢的人不是他的母亲,而是他自己。透过镜子,他看到一个拿着矿灯的瘦弱身影,正在呼唤着他的名字。而那个瘦弱的身影,正是他的母亲。
3)其实只有两个故事。第三个我还没有想好。
小宇

小宇你好:
我不知道我最近是怎么了,这么晚才回复你的信。真是太不应该了。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自己坐火车到了沈阳。那里刚下过雪,到处都是白色的,但是在那些空旷的大街上,只有我一个人,哦,还有很多很多的流浪狗。它们摇着尾巴,身上沾着黑色的雪,成群结队地跟在我后面。我停下脚步,它们就跟着停下来,我继续往前走,它们也继续跟着。我想要找你,但是怎么也找不到。后来,我蹲在电线杆下面,急得哭了出来。那些流浪狗都跑过来,用湿漉漉的舌头舔我的脸,或者是用脑袋蹭我的衣服,然后我就抱着它们,一起哭,哭了很久很久。
再讲一个故事吧。你的故事都很有意思,我很喜欢看。现在,我正写下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已经半夜十二点了,祝你好梦。吻你。
小惠

小惠你好:
那我就再讲一个故事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我的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小男孩,准确地说,是还是小男孩时候的他。或者说,他从未长大,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小男孩。很久以前,他跟他的爷爷和奶奶,住在一栋老房子里。老房子在一所大学的校园深处,背靠一座公园,叫“南湖公园”。现在,公园和老房子都已经不在了。在小男孩七岁那年,他离开了爷爷奶奶,去跟他的父亲住在一起。老房子变成了他的一座记忆宫殿。在这座宫殿里,房间变得越来越多。有的漆黑一团,有的欢声笑语,有的阳光明媚,有的阴雨绵绵。他把记忆像某种带翅膀闪着光的东西一样,储存在一个个玻璃罐里。就像《中央公园的鸭子》里的那个小男孩一样,这个故事里的男孩也养过一条鱼,但是不是金鱼,是一条草鱼,人们吃的那种草鱼。你肯定会问:为什么要养一条草鱼?原来,在他上小学时,有一次去春游,碰到了了一个叫“浑水摸鱼”的游戏项目。他的伙伴们都摸到了自己的鱼,可是等轮到他的时候,水池已经空了,什么都摸不到。他坐在草地上,悲伤地哭了。这个时候,一个穿防水靴的男人走过来,用带着烟味的手,像耶稣一样拍了拍小男孩的脑袋,让他别哭了,然后递给他一个装满水的塑料袋。小男孩打开塑料袋的一角,看到里面游着一条健康的草鱼,笑容立刻在他的脸上绽放了。那是小男孩养的第一个宠物。一条草鱼。一条本来会被人吃掉的草鱼。
回到家,小男孩把草鱼放到了父亲的浴缸里,因为父亲从来也不回家,总是在出差,就像一个幽灵,只会在他睡着后回家,在他睁开双眼前离开。有时候,父亲唯一存在过的痕迹,就是桌子上剩下的空酒瓶和花生碎,或者是门口打乱顺序的鞋,还有在他梦中依稀出现的,钥匙开门的声音。因为父亲从来不回家,所以他就从来不会用到他的浴缸,因此小男孩用父亲的浴缸来养鱼,也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草鱼很好养活,喂一点馒头渣就可以了。他趴在浴缸边,打开台灯,暖光照在水面上,使得上面出现细微的波浪,好像爷爷额头上的皱纹。他开始跟那条草鱼说话。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草鱼说,我没有名字,要不你给我起一个?他说,你是黑色的,我就叫你小黑?草鱼说,我已经不小了,在草鱼里面,我已经算是长辈了。他说,那就叫你老黑吧。草鱼想了想,说,行。他说,你在这儿过的怎么样?草鱼说,吃的还可以,就是地方有点小。他说,对不起。草鱼说,没事,我的同龄鱼都已经被红烧,或者是被清蒸了。和它们比起来,我已经算是很幸运了。他说,你放心,我不会让他们红烧你的,我也不会让他们清蒸你。草鱼点点头。他说,你出生的地方,很大吗?草鱼说,我出生在一个狭小的养鱼池里,里面都是和我一样的草鱼,挤在一起很不舒服,但是我在梦里梦到过。他说,梦到过什么?草鱼说,我梦到过一条宽大的河流,河水清澈,我在里面随意地翻腾跳跃,自由自在。说着草鱼闭上眼睛,睡着了。小男孩关掉台灯,拔掉插头,捧着它离开了厕所。他躺在床上,梦到自己变成了一条鱼,一直潜到很深很深的地方,虽然很深,但是太阳还是照得到。
那年夏天,小男孩和往年一样,在爷爷奶奶那里住了两个月。等再回到家,他发现,浴缸里的草鱼不见了。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那条草鱼去哪里了,因为他一直都没能鼓起勇气问他的父亲。
小宇

小宇你好:
请忘掉我上一封信里说的话吧。我在想什么呢,真是个大笨蛋。就当它没发生过,可以吗?你跟我说的这个故事很悲伤。你的那个朋友,那个小男孩,他现在还好吗?最近我常常想到死。你觉得人有灵魂吗?如果有一天,我不在这个世界了,我们的灵魂会到哪儿去呢?我觉得自己每天都戴着一个面具,上面只有一种表情,那就是笑脸,笑脸后面什么都没有。我想,每个人都有两个年龄,一个是身体的年纪,一个是灵魂的年纪。而我们的生命,其实都停留在某一个时刻。从某一天,某一月,某一年开始,我们就停止长大了。对于那个小男孩来说,他的年龄,也许就停留在草鱼消失的时候。那么我呢?我常常觉得,自己就快要撑不住了。或许,一切在我们生下来那一刻就注定了,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改变的。
小惠

小惠你好:
我很想见一见你,但是又很怕见到你。此刻我多么希望,我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天啊,这样我就有勇气买一张火车票,用那最后一天来到你的城市,哪怕只是能短暂地看到你真实的脸,听一听你的声音。你的声音一定很好听吧。还记得那个关于鱼的故事吗?我把结尾给改了。在这个新版本里,男孩的父亲打来电话,逼迫男孩在他回家前,把那条鱼扔到楼下的垃圾桶。男孩放下电话,决定孤注一掷,趁着父亲还没有回家,他把草鱼从浴缸里捞出来,装进塑料袋,系了一个扣,藏在校服的兜里,然后离家出走,一直来到北陵公圆的望湖亭。他站在湖边,看了看那条鱼,解开塑料袋,把它扔了进去。鱼把头伸出水面,像人类一样直立起来,盯着男孩看。鳞片在夕阳下闪着彩虹的光芒,就像肥皂水吹的泡泡。男孩说,快走啊,你自由了,你快走啊。那条鱼就像听懂了一样,摆了摆尾巴,眨眼就潜入湖底。在那个瞬间,男孩感觉自己的后背湿漉漉的,衣服纷纷从身上滑落,胳膊长出鱼鳞,双手化为鱼鳍的形状。紧跟着,他也变成了一条鱼,跳进黑暗的湖水,永远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小宇

小惠你好:
好久没有收到你的信了。你还好吗?这里又下雪了。
小宇

小惠你好:
我来上海了,还去信封上的住址找你了,但是没有找到。门后面是个老太太,她以为我是卖保险的,所以没有给我开门。我经常想起你,也经常看你以前写的信,每一次看都很开心。没事的时候,我总是在想,你现在会在哪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想,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一切才会变成现在这样。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了呢?
小宇

小惠你好:
很久没联系了。写这封信是想告诉你,我准备去美国上大学了。钱是我妈出的。谁知道呢,也许我毕业以后就会回来,也许我再也不会回来。我想我不会再写信了,我已经把一辈子能写的信都写完了,而且把它们都写给了你。谢谢你,你不知道你对于我意味着什么,但是,你知道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最好的故事是什么吗?就是在那个小说家写的时候,连他也不知道结局是什么,可是写着写着,结局就自己从笔尖浮现了出来。
小宇

二〇二四年的冬天,我收到一封信,信封上没有名字,用铅笔画着一个小男孩,手里抱着一只装满水的鱼缸,但是里面没有鱼。我看着那个信封,在那里站了一会。才把它给打开。信的内容十分简短。“小宇你好:我想来沈阳见你。方便时回信。我知道很多年过去了,如果你已经不在这个地址了,或者不想见我,那么请把这封信烧了。我都理解。小惠。”看完之后,我又重新看了一遍,然后回到房间,写了一封回信。“小惠你好:很高兴你能来。我在这里等着你。这些年来你都去哪儿了?背面是我的电话号码。小宇。”两周后,我收到了小惠的短信。“小宇你好。我已坐火车来沈。明日下午三点,北陵公园见。祝好。小惠。”
此时,距离我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已经过去了十年。
来到北陵公园的时候,雪已经停了。靠近西门的大松树下面,站着一个扎马尾辫的女孩,手里拿着半张饼,背着一个米老鼠的书包,看起来挺沉。我想,那个女孩一定是小惠。很多年过去了,她一点也没有变,可以说和照片上一模一样,甚至年轻了一点。这是可能的吗?这时她也看到了我,擦擦嘴,把饼放到一边。我说,什么时候来的?她说,吃过饭就来了,一直在看喜鹊。你饿吗?我这里还剩了半张大饼子。这张饼实在是太大了,我吃得很撑,可还是剩了一半。我其实很撑,结果却说,好啊,我饿坏了。她立刻变得很开心,伸出纤细的手腕,把那半张饼递给我。然后,我就一边费劲地吃着饼,一边跟她说起这些年的事。我说,我在美国待了九年,去年才回来。我去的是一座海边的城市。从上学的地方走回家,要走很久。整条路都在海边,我一边走,海浪就一边拍打在旁边的堤坝上,然后我就会想起你。每天晚上,我都会把那些信拿出来,看一看。久而久之,我把它们都背了下来。
说完这些,我们都陷入了沉默。我忽然意识到,很多年过去了,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她不是以前的她,我也早已不是以前的我了。这时她说,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吧。我说,好。她说,其实也说不上是一个故事,是我看过的一个电影。很老套的情节,讲一个男孩怎么怎么爱上了一个女孩,但是女孩不喜欢他,于是他就留了一封遗书给她,准备跳河自杀。可是在他抱着石头,一点点走进冰冷的河水时,女孩出现了。她跑过去抱住他,然后把他从水里拖了出来。男孩说,你别管我,你让我去死吧。没有你,我也不想活了。女孩说,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总有一天你会忘记我的。你会爱上另一个女孩,跟她结婚,生孩子,然后一起变老。到时候,你会庆幸自己没有淹死在这条河里,你会庆幸自己活了下来。这时电影就结束了。
我说,这样就结束了吗?
她说,对,这样就结束了。你喜欢这部电影吗?
我说,不喜欢。
她说,为什么?
我说,结局太美好了。
她说,结局好一点不好吗?
我说,也许在现实中,也有一个这样的男孩,那个男孩也会跳河自杀,然而和电影里不一样的是,没有女孩会去救他。他会一个人,在冰冷的河水里,一点点死去。在停止呼吸以前,他会想到很多很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但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我还没有说完,小惠突然凑过来,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下。她的身上有一股婴儿的清香。我下意识地伸出手,摸了摸她后脑勺那儿的头发。一种强烈的预感向我袭来,如同面前打了一道闪电。
我说,你不是小惠吧。
她的身体一震,往后退了退。
不是。
你是小萍?
她点了点头。
我们沉默了一会,她说,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一种感觉。你和写信的人很像,但是又不太一样,我也说不出是哪儿。
她想了想,又点点头。
小惠还好吗?
小惠已经不在了。
她也出国了?
我的意思是,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但是她的一部分,现在就在这个书包里。
她拉开拉链,露出一个白色瓷罐,旁边放着折叠铲和手电筒。她抱着瓷罐,轻轻把盖子打开,里面是一些灰色的粉末,参杂着没烧干净的碎骨头,还有烧之前剪下来的黑头发,黑头发里面夹杂着几绺白头发。我停顿了一下,问她小惠是怎么死的。她说,一个冬天的早上,小惠走到她们家附近的桥边,在兜里装满鹅卵石,然后从那儿跳进了河水。她留下了一封遗书。遗书里说,在她死后,尸体烧掉,骨灰要分成三份。其中的一份,就埋在北陵公园的松树下面,这样她每天都可以看到雪了。还剩两份骨灰,一份呢,就埋到她读过的小学后面的游乐场里,那里有一个假的北京站,假北京站的后面,还有一道假的长城。她说长城下面那个地方就挺好,挺安静,早上还有鸟叫,我们小时候老在那儿滑滑梯。另外一份,就撒到我们原来住的小区前面那个池塘里。原来她在那儿喂过鱼,难过的时候,还会绕着那个池塘,一遍一遍地走路。现在,游乐场已经关门,北京站和长城被推土机铲平,小区马上就要拆迁,池塘也将不复存在。只剩下这一份骨灰,我还没有撒。因为北陵公园还在这里。它不会被拆迁,也不会被填平,这些树,它们已经在这里伫立了几百年,还会一直伫立下去。时间还没有将它们击败。我觉得吧,我把她放在这树下的时候,你也应该在这里,见证这一切。她停顿片刻,酝酿了一下情绪,接着说,那些信,本来我只找到了三封。但是去年秋天,在那个旧小区拆迁以前,住我们房子的那家人,在一片松动的地板下,找到了一个月饼盒,里面有不少信,每一封都整齐地叠好,放在一起。他们把盒子给了我。我把里面每一封信都看了,而且看了好几遍。看完之后,我觉得,我好像一直以来都认识你。我甚至觉得,我爱上你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小萍讲完了。她站在那里,看起来就像是她姐姐的鬼魂。公园里的人越来越少,夜幕像一条条发光的小河一样降下来。那些老人和周围的松树一样,绕着小路,不停地走着,好像他们都已经穿好了干净的衣服,正躺在棺材里面,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又过了很久,公园里的人都走光了。漆黑的道路旁,只剩下我们两个。她从书包里拿出铲子和手电筒,递给我。雪地里有一些炸开的黄色,是撒来喂喜鹊的小米。我打开手电筒,从长椅上站了起来,她抱着瓷罐跟着我。路在我们的身后一点点消失了。我指着一棵大树,告诉她我爷就埋在那儿下面。又走了一会,我相中了一棵树,十分高大,等凑到下面,看到树上刻着一行极深的字,然而经过风吹日晒,已经面目全非。那些字是:爱妻王秀娟一九六八年葬于此。我说,这棵树已经有主了。她指了指远处说,那棵呢?虽然现在是冬天,但是到了夏天应该挺茂盛。我点点头,走到那棵树下,开始挖坑。小萍说等一下。我看了看她。她把手伸进怀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她说,这里还有一封信,是她写的最后一封,写完以后,就扔进了垃圾桶,后来被我给捡了出来。我没给任何人看过呢。你看看吧。我接过来,拿在手里,信很短,我半分钟就看完了。上面写着:
“小宇你好:我马上就要去跳河了,等我把这封信寄了就去。希望河水不要太凉。你知道吗?你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以后会遇到一个好女孩的,只可惜那个人不是我了。我实在是看不到希望了。二〇一三年一月一日。”
我继续挖着坑,不一会就挖好了。我把信纸铺平,和骨灰盒一起放到里面,然后拿起铲子,将黑土像糖霜一样洒在上面。洒了一会,信纸和骨灰盒都看不到了。我问小萍该刻点什么,她想了想,说就刻“姐姐小惠二四年冬葬于此”吧。我掏出瑞士军刀,把那些字,一个个在树干上刻出来。等刻完了,我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手。在寒冷的空气里,小萍握住我的手,像放一个热水袋一样,把它们放到怀里捂着。我触碰到她的肋骨,她很瘦,肋骨外面包着一层薄薄的纸,可是她的身体却像火炉一样温暖。漆黑的夜色里,我感觉自己正被亡者包围着。
两分钟后,我把手从她怀里拿了出来。
她说,还冷吗?
我说,不冷了,一点也不冷了。
她说,那就好。
一只灰蓝色尾巴的喜鹊从树上下来,飞到我的肩膀上,我伸出手,轻轻碰了碰它的尾巴,它没有躲。大门早已关闭,我们爬上一个雪堆,从那里翻出公园的围墙。
她说,小宇,你还在写小说吗?
我说,偶尔写一点。
她说,你会把这些事写到小说里吗?
我说,也许吧。我从来不敢把自己放到小说里。我的人物都是死的。
她说,不要这么说,当你把他们写在纸上的那一刻,他们就活了。
我点点头,说,你现在想去哪儿?
她说,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还可以去哪里。
我说,做点开心的事吧。我已经看够死亡了。
她说,唱歌算不算开心的事?
我说,当然算。
她说,那我们去找个地方唱歌吧。我想唱歌了。
好,我说。去唱歌吧。

2024年4月 初稿
2024年9月 二稿


NEXT: 戴紫色假发过圣诞节的女孩
哈德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