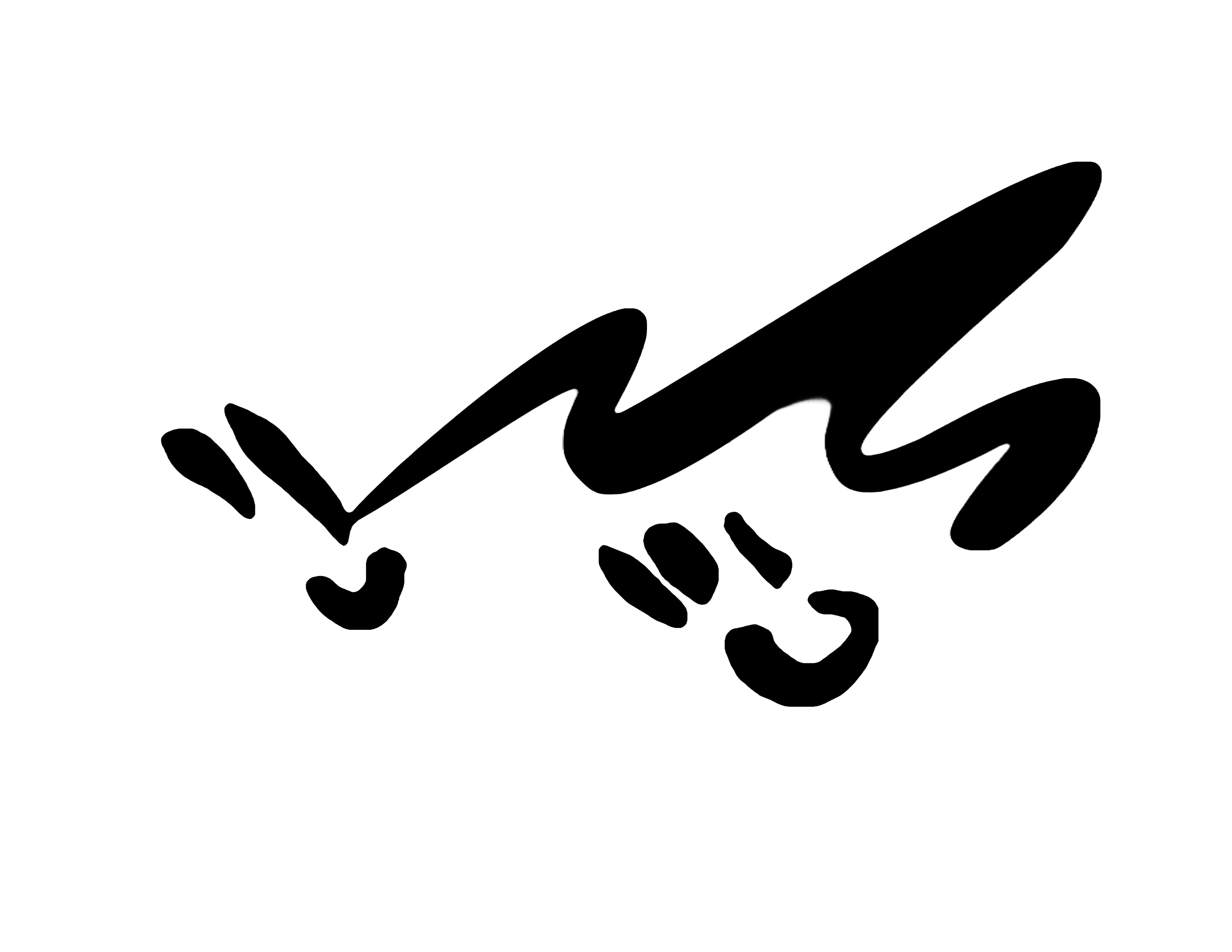原乡·逃逸·回溯
——以两岸经验为基础创作的同时代”半虚构”文学的异质性
3D
编者按:
上学时,我们便执着于什么是作者的本意。长大后,我们又执着于辨别故事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好像去伪存真是唯一可能获取知识的方式。然而,后现代主义思潮告诉我们,“事实”本就是被建构出来的,当“虚构”以一种投射的方式承载了作者的个人生活经验,又反过来影响现实,或许我们有必要在“虚构”与“现实”间寻找一个中点。
对于半虚构的作品我们并不陌生,尤其是看电影的时候,片头或者片尾经常会在屏幕上出现这样一行字: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说明电影故事的情节发展和故事样貌和现实的情况不一样,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重新处理和创造,但故事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特点往往是真实可感的。根据我自己的文学阅读经验,时常看到虚构和非虚构的二元对立的分类,但很少有“半虚构”这样一项分类。或许类似的作品都被归纳入了虚构分类中,但是我仍然认为一项单独的“非虚构”分类很重要,他们常常是对于过去或者现在的经验的总结加入自己的理解和思考从而创作出新文学作品,基于社会事实且强调社会现实和时代特点,却又不仅限于此。我认为这种文学是绝对有别于完全虚构作品的。
本篇论文,我想以朱天文与王安忆的作品为案例来探讨一种非二元(虚构/非虚构)的以成长背景及性别视角等经验为主而带来的“半虚构”文学创作,同时进一步挖掘在相似主题之下由于两岸社会、文化、政治经验的不同给其文学创作带来的异质性。
首先,我认为两位作家的成长背景所带来的经验写作是具有异质性的。“家族,又称宗族,它是以家庭为核心实体的以血缘与性关系为纽带的人类社会自我协调的结构性产物和基本单位,是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双重互动的必然结果。” 如上所述,通常家族既有‘实’的一面,即社会的外观形态;又具有‘虚’的一面,即文化表征意义。大陆作家王安忆创作的《纪实和虚构——创造世界方法之一种》和《伤心太平洋》两部长篇是关于父辈家族记忆的书写。台湾作家朱天文关于父辈的书写虽然没有形成长篇巨著,但也以中篇或短篇的形式出现,比如以父母为原型创作的《叙前尘》、《那一天》、《桃树人家有事》等短篇。她们不约而同地选择还原自己父辈的形象,将其放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中,通过书写他们战争中的经历,显示着个体由于不同的政治选择所带来的不同的命运,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作家的创作异质性。
王安忆和朱天文基本处于同一年龄段,都出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长于七八十年代。而众所周知,二十世纪社会正值急剧变化的转型时期,使作家不断调整着她们的创作空间。本为“原乡”的乡村在她们的创作中均有二次不同的书写,并且她们对乡村(或眷村)的感情也经历了由“离散”到“归来”的变化。为什么对同样的土地却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基调?我认为对于二位的时间因素的介入是重要的原因。这里的“原乡”有着意指着作家心向往之的地方(可能是地理上真实存在的,也可能是回忆中的,又或是梦想中的)。两位作者试图回溯自己的过去的家族经验,希望通过发现父辈找回自己。的确,“推动我们力量的并不是恋母弑父情结,而是‘肖父’的愿望,从家族历史中夺回自己,推之如不朽的愿望。最终我们顶多能塑造点什么——一样东西,或我们自己,然后弃之于迷惑混乱之中,把它当祭品或礼物,献给生命的长河。” 而父辈无奈中的坚守,对世事的淡泊深刻地影响着后代们的世界观,使她对人生有了深刻的体悟。例如不再用意识形态、主义、信仰(及其所衍生的政治阵营立场)来分出所谓的“好人”和“坏人,而是把人分为热心的、充满理想主义、利他的、善思省的人和冷漠的、现实的、只为自己盘算的人。从父亲的人生观中,朱天文提炼出了超越阶级的人性观,体现了对父辈和自我的反省意识。或许,对家族命运的关注就是对人类对“原乡”追寻的终极关怀。在这层意义上来说,关于家族的历史追寻或许就反映着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决心。这种家族书写中的漂泊和无依无靠契合了八九十年代社会的现实,“在这个剧变的社会中,个人的独立化也加深了人们的孤立感和无助感,家族的存在可以通过家族认同、血缘关系给人们以某种心灵上的归宿和寄托。” 同时,这种家族的经验书写也与解构了传统家族小说的神圣性和权威性的新历史主义(Neo historicism)小说息息相关。以民间的近乎戏谑的方式讲述庞大的家族历史,解构被意识形态处理过的家国记忆。王安忆在对父辈留给自己的精神财富中反复咀嚼,反思,建构起属于自己的世界。朱氏姐妹则在父亲猝然辞世的遗憾中回溯自己的经验。父辈们好像一面镜子,在不断地催促着后辈们你从哪来,曾是谁等。这些经历仿佛是她们生命的起始,亦是她们宝贵的创作的经验。同时,父辈作为革命者的经历,也折射出国共两党的恩怨纠葛,反映大时代中个体的孤独无依,体现了她们关于人性的思考,也体现了文学基于非虚构的历史的一种深刻反思。
其次,我认为两位作家笔下的时代女性视角下的经验书写同样存在着异质性。二位均创作了许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性角色,充斥着对于女性时代命运的反思和拷问。王安忆创作的小说《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是一位逃逸中的女人。在生活空间上,她经历了从弄堂到公寓到邬桥再到平安里,随着这些空间的转移,她的身份也发生了由女孩到外室到单身最后到母亲的转变。她人生重大的改变和这些空间的转变密切相关,可以说,她在每一次的重大人生改变的过程中都选择了短暂的逃逸,来调整自己的心态,进而缓和与现实的张力。经王安忆对于女性逃逸命运的探求在世纪末得以再现。在她的另一个作品《月色撩人》女主角提提也是一个“逃逸”女人的形象。她从“什么都是可预测,一眼就看到底”的小城市来到大都市上海,成为所谓的都市“白领”。开始了不断游走在各式各样的男人中间的旅程。几十年前的王琦瑶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爱丽丝公寓”中的李主任,几十年后的提提们也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现代意义上公寓里的“新贵们”,虽然时代在变化,一种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心理却依然存在,不曾改变。相信王安忆两部作品中女性命运的对照不会只是一种无意或者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深刻的反思,甚至是基于自己的过去经验的一种思考的经验改写。
和王安忆笔下的“逃逸者”相比,朱天文笔下的女性则算是已经失去了空间上的兴趣,把自己或者封闭到一个固定的环境中,或者即使出外,也逃出人际交往的圈子,可以看作是一种将自我放逐的时代逃逸者。如《世纪末的华丽》中的米亚,她终日逗留在自己的九层公寓观察天象,她的屋子像药坊,养满屋子干燥花草;她的浴室遍植君子兰,非洲堇,观赏凤梨,孔雀椰子,各类叫不出名字的绿厥。以及毒艳夺目的百十种浴盐,香皂,沐浴精,彷若化学炼制室。这是一座公寓只有她自己的公寓,是孤岛中的孤岛,而她就是孤岛中的个体。爱情居然带给她“好陈腐的气味”“令她想起“呆滞出汗的窗树,”和“像橘红塑料碗一样蹲满树枝”的木棉花,而老段却往往错觉他跟一位中世纪僧侣在一起。
如果说王琦瑶的“逃逸”更多的来自于与外部世界的压迫,逃逸只是为了暂时的调整,提提的逃逸则是为了明确的物质性,为了生存。而到了世纪末的台北,她们的逃逸更多的是逃回自我封闭的心灵公寓。作为生存空间的公寓从此不仅仅是一种观察都市的视角,更是窥探瞬息变化下女性时代命运的一扇窗口。“米亚们”在公寓里从事的活动也与现代人无关,却具有农耕时代的单纯和原始。她们的侍弄花草已没了欣赏的闲情雅致,而充满了企图挽留住时光的虚妄。她“对城堡里酣睡市人赌誓,她绝不要爱情,爱情太无聊只会使人沉沦。世界绚烂她还来不及看,她立志奔赴前程不择手段。物质女郎,为什么不呢,拜物,拜金,青春绮貌,她好崇拜自己姣好的身体。” 她的爱情和王琦瑶的一样是无望的,但王琦瑶的无望是物理空间上被撤除的,是伴随爱人的逝去而永远无法得到的。米亚的爱情却是明知无望却偏要尝试的。和提提们一样,这个世纪末的女巫在爱情上无所谓什么得失,不图任何回报,她的爱情是建立在相互取悦的基础上,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上的共同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婚姻观念于“米亚”已经失去意义,她需要为自己规划未来,她必须要学会独立于感情之外。王安忆与朱天文创作的“逃逸”的女性形象相互间有着某种同构性,这种同构性又有某种历史经验延续的功能,似乎是几千传统文化濡染的结果。多少年来女性无法主动地把握自己命运,只能通过不断地逃离或者被动地隐忍来面对人生。相比较而言,我认为值得一提的是,受后现代影响较大的朱天文笔下的女性形象更加自我和超前,而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形象则略显含蓄和节制。
再次,通过网络搜索及文献阅读,我调查到了两位作者的家族经验,想以此为出发点以总体的角度来思考两者经验创作的异质性。王安忆和朱天文均出身文学世家,也由于父辈的庇荫初登文坛,即受关注。而其父辈的家族历史也为她们的创作提供了珍贵的精神财产,成为她们写作的出发点。由于家族经历本身就包含文本的自足性,再辅以文学的审美就构成了家族书写的历史价值和审美意义。王安忆成长在社会主义时期,有着苏俄文学阅读积淀;朱天文所拥有的是深刻的台北后工业文化体验。这些区别又形成如下创作差异:世俗日常人生,在王安忆笔下被定为暖色调,而朱天文的都市人基本决绝于日常。在日常悲喜冲突观照层面,王安忆笔下传递了新旧、中西夹缝中人的不安和挣扎,个体与族群冲突中人的自失与自足,朱天文笔下则重在表现个人与主流龃龉中人的迷惘与失落。两人都涉及“末世感”,王安忆作为温暖的“人道主义者”(humanitarianism),虚无中尚存希望,朱天文则是因抵抗“现代性”而陷入了精神焦虑。 二人都共同注视女性生存之艰,王安忆笔下新女性为爱而生,备尝艰辛,而朱天文笔下都市女性则为破除男性神话走向了危险边缘。在女性身体的微观考察上,王安忆笔下的新时期女性解放了被禁忌的肉身,朱天文则看到后工业时代的女性将肉体挥霍到了极致。在形象叙事方面,王安忆属于一种兼有意象化叙事的直观写实叙事,朱天文则是兼有意象化叙事,又有背离碎片化叙事。
最后,回到我一开始提出的文学新分类:半虚构文学。我以为若是没有如此的时代变迁,家族变化,自身性别视角等经验的积累,或许两位作家也不会创作出如此建立于现实反思的个人成长和性别视角主题之上的作品。这些基于自身或是他者转述的基于经验的创作,便是我认为的半虚构文学,是有别于纯虚构文学的。这样的一种单独分类,我认为可以更好的激励读者去了解文学背后的历史叙事,以及作者作为个人的经验积累。若是阅读时不结合着作家们的种种经验,作为读者或许便也很难理解并共情部分文学的更高内涵与深层含义,导致对于文中所探讨的种种异质性鲜有察觉。
参考文献
[1] 李佳.末世之花,淡然之美——尹雪艳与米亚精神层面上的承继关系[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4(06):70-73.
[2] 安镜伊. 从青春书写到世纪末观照[D].吉林大学,2011.
[3] 赵学勇.家族文学研究的攻坚之作——评杨经建《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J].中国文学研究,2006(04):110-112.
[4] 王德威:《从〈狂人日记〉到〈荒人手记〉——论朱天文,兼及胡兰成与张
爱玲》,《世纪末的华丽》,台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
[5] 洪士惠:《上海留恋与忧伤书写——王安忆小说研究》(硕士论文),台北淡江大学中文研究所,2001.
[6] 杨经建:《家族文化与 20 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长沙:岳麓书社,2005.

NEXT: 艺术部
wushushan9@gmail.com